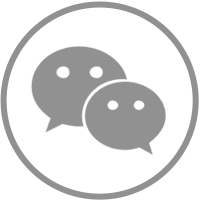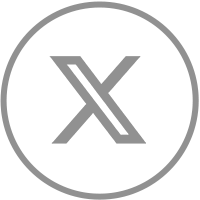一九一六年底,進士出身又有留洋背景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此消息一經公布,《大公報》便發表《為大學校前途祝》,預言他「定能為教育界放一異彩」,此後十年蔡元培果然把一個八表同昏、烏煙瘴氣的舊式京師大學堂(當時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逛八大胡同),變化成新文化運動的戰鬥堡壘,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至全國,獲益於後世。
蔡校長甫一上任,首先聘《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陳獨秀為人圭角畢露,鋒芒逼人,與蔡先生風格絕異。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講授邏輯學,留美博士胡適講中國哲學史,衣着馬褂拖着辮子的辜鴻銘教授英詩,稱其為外國大雅小雅、國風離騷,贊助袁世凱稱帝的劉師培講授「三禮」、《尚書》和訓詁,精通音韻訓詁的黃侃講授《文選》,語出驚人的錢玄同講授音韻學,還有因寫通俗小說被人瞧不起的劉半農,戲曲專家吳梅。此外尚有許多名士,馬敘倫、沈兼士、朱希祖、沈尹默、陳漢章、陶孟和、李大釗等,一時人才濟濟。留德歸國的楊懷中(昌濟)應邀從湖南來京,授西洋倫理學史。梁漱溟當時二十多歲,既無留學背景,亦無舊學功底和著作問世,僅在《東方雜誌》發表了幾篇佛教哲學的文章,被破格聘為北大講師。開放女禁,允許女生入學,第一位入北大的女生王蘭,是王昆侖的姐姐,今天看來平常,當年卻是前衛,那時的北京,女人尚未被允許進戲院看戲,男女同校在當時的歐洲,也只有幾個最發達的北歐國家可以做到。
馮友蘭說,「若論新文化運動的起源,應該從一九一七年初蔡先生到北大當校長那一天算起。」這十年,北京的政權由軍閥把持,頑固腐敗的勢力如猛獸,但新思想的浪潮如洪水,蔡先生幽默地說,「可算洪水與猛獸的競爭」。如果沒有蔡先生的器局和卓識,就不會有各路英才的匯聚,若沒有這些英才,就不會有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興起。如羅家倫所言,「以一個大學來轉移一時代學術或社會的風氣,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陶希聖和羅家倫同為當時北大在校學生,他也說,「這一風氣的改變,把當時北洋軍閥和政客的社會基礎給打壞了。」洪水到底是勝過了猛獸,林白水、邵飄萍、李大釗、史量才的遇害,並不能阻擋軍閥覆亡的命運。
在蔡元培的鼓勵下,北京大學成立了各種學會,少年中國學會、新潮社、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新聞研究會、中國畫法研究會等。這些研究學會,經過種種努力和擴展,對未來中國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蔡元培本人親自主持了進德會。北京大學學生多有成為棟樑之才者,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江紹原、俞平伯、馮友蘭、陶希聖、許德珩、段錫朋等等不勝枚舉。
後人多知蔡元培新舊資望備於一身,生逢其時,得到了施展,對於他「萃中土文教之精華於身內,泛西方哲思之蔓衍於物外」卻了解得少。
傅斯年說:「蔡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此兩種偉大文化,具其一已難,兼備尤不可。先生殁後,此兩種偉大文化在中國之寄象已亡矣。至於復古之論,歐化之談,皆皮毛渣滓,不足論也。」
蔣夢麟認為,「當中西文化交接之際,而先生應運而生,集兩大文化於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學足以當之,其才足以擇之」。
(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