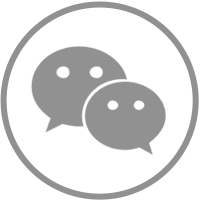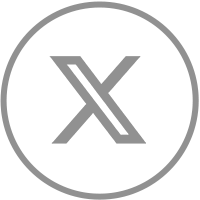2024年美國大選,西方主流視為事關美國乃至全球未來四年以及整個民主體制的命運。自2008年以來,西式民主在全球就處於衰落狀態。在這個背景下,美國的走向自然是舉足輕重。在西方自由主義眼裏,特朗普是一個不承認選舉結果、煽動暴力、歧視女性、散播陰謀論的極端民粹主義者,而且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等「威權主義者」互相欣賞。不僅民主黨候選人哈里斯,就連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米利,都稱特朗普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者」。因此這樣一個人物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將是對西方民主制度的重大否定。
美國制度糾錯機制已失靈
共和黨在特朗普的帶領下不僅以巨大優勢贏下總統,還有參眾兩院、州長、州議會,勝利可謂空前。這已經不是偶然和例外,而是主流美國人民做出的選擇。一個長期自詡「民主燈塔」的國家,就這樣在世界各國矚目之下變身全球極端民粹主義的領袖。
冷戰結束後,美國學者福山以「歷史終結論」而名噪天下:提出冷戰的結束標誌着人類政治歷史發展已經到達終點,歷史的發展只有一條路,即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然而,早在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當選時,「歷史終結論」已經被無情終結。只不過固執的福山仍然寄希望於2020年拜登,並以此作為美國仍有糾錯機制和能力的證明。但2024年大選前幾個月,福山在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卻坦承:美國不再是現代民主的榜樣。他不知道美國的制度是否足夠強大能夠抵擋住特朗普的回歸,美國正處於巨大的危險之中。現在特朗普以毫無爭議的大勝再度入主白宮,可謂美國制度的糾錯機制已經失靈。
如果從歷史的眼光看,兩百多年前,美國的政治體制還是超前和先進的,特別是它的選舉制度,既沒有直選的激進,也沒有議員選總統的保守,而是一個折中:民眾直接投票,產生的選舉人再選總統。既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也設置了安全閥,能防止民粹或者極端主義者獲得權力。
然而,以特朗普兩度當選為標誌,這套制度今天已經無法有效運作了。一方面西方以及效仿西方的國家普遍實行了直選,美國的制度顯得落伍。特別是候選人贏得普選票但卻輸掉大選的現象一再發生,體制的合法性不足。另一方面安全閥失效,無法阻擋特朗普這樣的政治人物。
如果和兩百多年前相比,今天的美國制度有兩大不同:一是實現了「一人一票」的大眾普選。二是全球化。這兩者的化學反應直接導致了今天的政治衰敗。
美國立國之初,所謂的民主是相當有限的,只有有財產和納稅能力、受過教育的白人男性才有投票權。這種僅限於精英的民主相對容易形成共識,也有共同的底線,分歧也並不是不可化解。當然,即使如此,仍然發生了利益不可調和的美國內戰。
西方近代精英民主的問題在於執政者往往忽視沒有選票的民眾利益,貧富差距極其懸殊,階級矛盾激化,特別是在歐洲一再引發革命。為了回應危機,西方一是經濟上讓步,比如縮短勞動時間、提高工資、建立福利制度等。二是政治上妥協,逐步擴大投票權,直至實現「一人一票」。在這個過程中,歐美逐漸形成了中產階級為主導的社會,並一直到冷戰結束都運作良好。此時,「一人一票」的負面後果並未顯現。
冷戰結束使得囊括所有國家的真正全球化成為現實。以美國為首的資本橫掃全球,資本的盛宴和狂歡在世界每一個角落上演。這導致兩個後果:一是西方去工業化導致中產階級萎縮,最窮和最富的群體反超過50%。二是大量的移民在全球流動,並日益明顯地改變了西方的種族結構。
此時,「一人一票」與全球化開始發生猛烈的化學反應,並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後果:特朗普的選票主要來自低收入、低學歷的白人群體,特別是全球化的受害者「鐵鏽地帶」。
西方民主難以適應時代變遷
客觀而言,歷經兩百多年民主實踐的美國人民是很了解兩大政黨的候選人,也深知不同的選擇對美國意味着什麼。但艱難的現實生活使得多數美國人放棄價值而選擇價格。這一幕曾在人類歷史上多次上演,特別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德國。
從理論上講,特朗普任期不過四年,他也不可能廢掉國會和最高法院,美國三權分立的框架依然存在。但是當他能掌控所有國家機器的時候,他當然不需要這樣做。
更重要的是,如果回望這八年,五次更換黨籍、2012年才又加入共和黨的特朗普對共和黨、對美國進行了巨大而又成功的改造。他和他的支持者已經從局外人變成了建制派,八年前的建制派要麼加入要麼出局。2016年,共和黨重量級人物比如布什家族集體表態不會支持特朗普。但今年特朗普勝選後,小布什卻立即表示祝賀,並說「這次選舉的投票率是我們共和國健康和我們民主體制力量的標誌」。
2016年,大企業還與建制派協商如何阻止特朗普,華爾街也倒戈支持民主黨。但今年以全球首富馬斯克為代表,大財團紛紛表態站在特朗普一邊。世人無法想像,再過一個八年,美國會變成什麼樣。
歸根結底,西方現代民主制度既有先天的結構性問題,又難以適應時代的發展和變遷。特朗普當選就是兩者的必然產物。他的當選也預示着「地理的西方」會一直存在,這套「制度的西方」則會消失。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