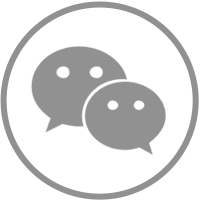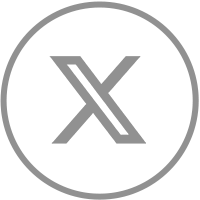還是從讀詩開始吧──
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園裏幹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上。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佔有。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遭受的不幸,
我都已忘記。
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並不使我難為情,
我的身體裏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看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這是波蘭大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作品,譯者西川,這首詩有很多譯本,之所以選這個譯本,主要是因為它的倒數第三句,「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並不使我難為情。」我認為是所有譯本中最好最精彩的,而恰好這句是整首詩的「詩眼」。再看看其他譯本,限於篇幅,也只看倒數第三句:「想到曾經我是同一個人,並不使我羞愧。」這是胡桑譯本,也還好,意思還是這個意思,但「我」在不同的歷史時段必然存在的變化被淡化了,也許譯者沒有聽說過特修斯之船的故事;「想起過去也沒有困窘不安。我的身體感覺不到痛苦。」這個譯者是馬永波,他把這個句子拆成了兩句,這倒不是問題,關鍵是詩中之意只是「青春無悔」這麼簡單嗎?米沃什無論如何也不是汪國真;「想到我曾經是這同一個人並不使我難堪。」李以亮譯本嚴謹平順,亦信亦達,就是不生動,沒有達成詩意上的精絕;「想到我曾是那同樣的人並不使我難受。」沈睿譯本問題較大,「同樣的人」,同的是哪樣?含混,指代不清,可能是最失敗的譯法。還有幾個譯本,這裏就不一一引述了。
西川譯本的成功之處,在於把「我」這個抒情主體,做了歷時性的切分,這種看似刻意的操作,恰恰呈現了「我」作為一種脆弱的存在,在時間風暴中必然發生的變異。寫到這兒,不禁想起木心一首只有一個句子的詩《我》:「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哪。」這是在寫我還是在寫雪?都不是,其實他是寫路,由於天昏地暗大雪紛飛,迷路就是「我」的必然處境。在這樣的處境中,人的命運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而這個不確定性帶來的也是「我」的變數。
小說和電影裏經常看到這樣的場景:故人重逢,面對一方的滄桑衰老,終於相認後的第一句話大多是:你都經歷了些什麼啊⁈由此可知,人是會經歷巨變的,而且這個巨變甚至是難以避免的,因為時間和社會境遇都會勢不可擋地參與到人的命運之中。由此可知,在「今我」和「故我」之間,山重水復,天塹通途,那些不可預知的道路,我們走過路過,終究還是錯過了,因為人無法回頭,時間不可駐留,我們一路走來,沿途留下一個個曾經的我,而帶在身上的天知道還有多少最初的原型。如果是一個在精神上保持自覺的人(所有詩人都該是),那麼「今我」永遠會處於對「故我」的追憶和辨認之中,同時反觀自照,以「故我」為坐標,辨別方位,校準方向,不斷朝着「認識你自己」的目標靠近。時人常以「出走半生,歸來還是少年」相期許,這其中的深意是什麼?是說半世為人,雖然塵滿面,鬢如霜,但我們初心未改,熱血難涼,攬鏡自照,還能窺見眼眸中的少年星火。
如此看來,「今我故我同為一人」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甚至可以稱之為奇跡。從「故我」到「今我」,其間必然經歷了無數探尋、堅持、幻滅、背叛、追悔、回歸、重建的曲折歷程,所以,也只有把一個混沌籠統的「我」切分開,才能進入波詭雲譎的命運,在不同之我的比對映照中呈現生命本身所必然包含的複雜性,也才能在米沃什的雲淡風輕中暗暗標註生命的重量。
米沃什是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意義的經典性詩人,他生於立陶宛,早年曾任波蘭外交官,後輾轉至美國,長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雖然身處英語世界,但他一直堅持用波蘭語寫作。他的詩作既有對精神世界的洞察與探索,也有對社會歷史的記錄與參與。
一九八○年,米沃什由於「在自己的全部創作中,以毫不妥協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滿着劇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脅」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在名為《詩的見證》的演講中曾說「詩歌必須意識到自己『可怕的責任』,因為詩歌不是純粹的個人遊戲,它還賦予『人民那偉大靈魂』的種種願望以形狀。」由此我們可以想像,以米沃什個人經歷的顛沛流離,以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特別是波蘭歷史的殘酷曲折,米沃什的詩歌創作該是承擔着怎樣的歷史重壓。然而,這首創作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禮物》,卻以波瀾不興的寧靜語調抹平了歷史風暴。
彼時詩人年逾六十,已經在加州度過了十年左右相對平靜的校園生活,而在世界範圍,雖然不斷有局部戰爭牽動人的神經,但冷戰代替熱戰還是以新的秩序重構了世界格局。這時候,「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佔有。/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這樣樸素的詩句就顯得尤為意味深長:天知道多少殃及眾生的災禍,皆是起自佔有之心。命運在牽動大風大浪之後,「我」和蜂鳥都在平靜地勞作,人和世界兩不相欠,大海,這永恆的存在依然存在,帆影在望,一種蘊含希望的秩序正在有效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