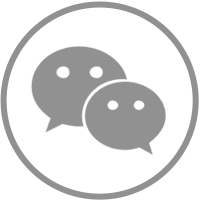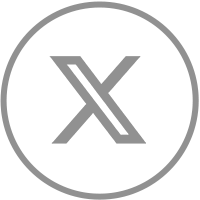做頓可口的菜豆腐,工序複雜。記得早年間,天不亮,娘就把泡好的黃豆放到石磨裏磨。伴隨磨盤的轉動,乳白色的豆漿源源不斷地流進水桶裏。等過濾出做豆腐用的豆漿,豆渣就成為做菜豆腐的原料。做菜豆腐的菜,主要是時令菜,春天是小白菜和野菜,冬天的主角是蘿蔔和大白菜,往往用的是大白菜外層的老葉子。不管哪種菜,先用開水焯一下,濾除苦味兒,再將其攥成菜團,擠乾多餘的水分,切碎備用。豆渣倒入鍋裏煮開,加入切好的蔬菜,豆子的醇香和清新的菜香混合在一起,掀開鍋蓋,香氣撲面而來,激活胃裏的饞蟲。
二○一三年清明節,我帶上妻兒回到老家看望父母。第二天一早,娘就為我做了我最喜歡吃的菜豆腐。頭一天夜裏就挑揀好了黃豆,放在瓷盆裏用水泡着。把黃豆選好、泡好、磨好這是第一步。為了吃個新鮮,天剛亮,父親就去自家菜園拔回了一筐帶着露珠的青枝綠葉的小白菜。娘安排晚輩到鄰村磨了黃豆糊子,就忙着摘菜、洗菜、切菜,幾個盆倒騰着,叮噹響。煮的時候需要細心掌握火候,防止豆沫溢鍋。娘一會兒往灶膛裏續柴火,一會兒掀起鍋蓋觀察,有時還用勺子舀起來看看。
吃早餐時,我們圍桌而坐,一人一碗香氣四溢的菜豆腐,還有辣炒豆腐,一人一個剛買的新小麥煎餅。大家吃得很香甜。吃到一半時,我剛把一口菜豆腐填進嘴裏,突然發現碗裏的菜豆腐上有半隻青蟲。那樣子是被刀剁斷的,蟲子身體的顏色和菜色基本一樣,只有蟲子的頭是黑的。雖然蟲子還在碗裏,但彷彿已經被我吃到了嘴裏。
瞬間,我胃裏翻江倒海,一陣噁心直衝喉嚨。但我硬是把它壓了下去,緊緊閉上了嘴。不能說啊!如果說破了,就毀了娘忙活兩天的歡喜,也打碎了一家人難得的團圓。娘年紀大了,眼神不濟,漏掉一兩條小青蟲再正常不過。要怪,也該怪我這個眼力好的兒子,只顧等着吃,卻沒伸手幫一把。看着娘心滿意足的笑容,看着她額前那縷白髮和那雙操勞的手,我哪裏還忍心讓她有半分難堪?那口菜豆腐在嘴裏打了個轉,被我生生嚥了下去,又悄悄把那另半條蟲子挑出來扔到了地上。我的這個動作,還是被娘發現了。
「菜裏有東西嗎?」娘放下手裏的筷子,問我。
我趕忙說:「沒,沒有,不小心被菜噎了一下。」
娘沒有再回話,只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自責道:「我老了,不中用了。」
「今天這豆沫味道很鮮!」我知道聰明的娘已猜到我吃到了什麼不好的東西,趕忙回應道。
我和娘的對話,大家誰也沒注意,談笑中,話題很快就被岔開。
那碗菜豆腐,我是在狼吞虎嚥中吃完的,也令我終生難忘。如果我吃慢了,娘肯定會發現其中的端倪。在吃飯的過程中,我幾次強忍着淚水,心裏一直在想:在苦水裏泡大的娘,省吃儉用,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也千方百計讓一家老少吃飽穿暖,這是多麼了不起。這種能觀察到、能享受到但又難以言明的品德,讓我高山仰止。孩子們一個個長大、成家立業了,娘依然牽腸掛肚、放心不下。我們偶爾回家一趟,娘總是想方設法做每個孩子最愛吃的飯菜,這份恩情我們怎麼也報答不了。我最樸素的想法就是,說啥也要讓娘高興、不給娘心裏添堵,這是最基本的道德水準,也是高尚的人性表達。我一直慶幸我當時沒有順口告訴娘,沒說破我吃出半截青蟲的事。吃這一碗菜豆腐,吃的是心中美好的記憶,品的是一家老少團聚的美好時光,嘗的是一縷濃得化不開的鄉愁……
我妻子知道我喜歡吃菜豆腐,也慢慢學會了自己做。我不時能吃上用新鮮蔬菜做的菜豆腐。先喝一口菜豆腐的清湯,嗨,真是清爽的美味呀,沒了菜的生澀或青苦,只有菜的清香、豆香的醇厚和熱湯的溫暖。我妻子還找到了保存菜豆腐的新辦法,當頓吃的放鹽;第二頓吃的,吃時再放鹽,能保持菜的色澤不變;如果長時間保存的話,就乾脆放冰箱冷凍起來,顏色和味道不變。菜豆腐,早已超越了溫飽,成為滋養精神的美食,承載着詩與遠方的遐思。
童年總會消失,夢想不能幻滅。在滿桌雞魚肉蛋的今天,在異地他鄉,吃到家鄉的味道「菜豆腐」是一種福分,有遇到知音般的欣喜,那是鮮活鄉愁的一縷「地氣」,一股「人間煙火氣」。
每次看到菜豆腐,我便會想起當年娘做的那一碗,那菜豆腐的滋味更稠、更鮮、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