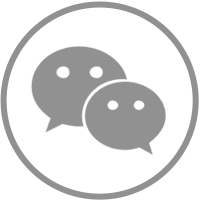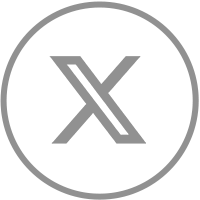我所在的南方城市此刻並未下雪,定居武漢的同鄉作家祿哥分享來武當山金頂一位道士拍來的雪景,厚重、沉靜,把猩紅的宮牆和瓦黑的飛簷渲染出一片深遠浩大的氣象。這才是一場雪該有的樣子。我們該有多久沒見到一場像樣的雪。尤其我所在的這座城,多年來,每年只在最冷的時候象徵性下一場雪,雪粒細小就算了,才飄到半空就化了,敷衍吝嗇至極。想看一場雪,唯有把視線轉向中原,望向北方。
不認識那位道士,也不知道他是哪裏人。我猜想,已在我家鄉的這座名山修行了很多年吧,他應該早已成為山的一部分。祿哥說,等我回了老家上了山,他要把道士介紹給我。很慚愧,我一個武當山的子民,竟然對道教一知半解,皮毛都不懂。但一個道士在雪山之巔打坐入定,是我更想看到的畫面。那時的道士,頭頂高盤的髮髻或許夾雜着細長的雪,黑色的布靴和一身藏青色的道袍,必定積滿了空中飄來的雪花。身後積雪覆蓋的百年古松,偶而也會不時地饋贈他一些,悄悄放在他消瘦的肩膀上。但他並不在意,他與武當的雪融為一體已很久,宇宙時空都在他不動如山的身姿中神遊。
我和祿哥認識了有些日子,始終未得機會見面。我知道,我與他的道士朋友相識的日子也遙遙無期。因為我已經好幾年沒回鄉,更沒機會登上武當山。飛雪中的武當山,記憶中該是二十年之前在家鄉做媒體記者上山採訪時見過吧,可惜對雪的形狀已模糊至極,雪中遇到什麼人也毫無記憶。只記得自己那時還是一個熱血激情抱負宏圖的青春少年郎。自從離鄉到外地謀生,就與武當的雪再無交集了。
這世上,與任何一個人、一座山、一座城、一場雪相遇或再會,都不是隨隨便便的事,要積攢足夠多足夠深的機緣。
自然,我也明白,即便一些地方一些城市並未下雪,一些人早已遠離,一些事已消散,也無妨,很多雪會下在你心裏。無需身處高山與深林,只要你心裏有雪,想下的時候,它隨時就會簌簌而落,不分節氣不分晝夜不分場地。如今,有些雪已墜入隱塵,有些雪還在雲端孕育,有些還在蒼茫空域裏遊蕩。每個人,最終也只是一片雪,在時間的長空裏滑過。每一片雪在空中滑翔的痕跡,是我們用盡一生的努力。
正有些許感傷,祿哥發來微信說,家鄉的五弟自家每年都釀房縣黃酒,已請他快遞了兩大桶給我,剛發貨。看着快遞信息截圖,我又笑了,看來,在下一場雪來臨之前,就能喝到家鄉人釀的美酒了。那酒裏,應該有家鄉大雪的味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