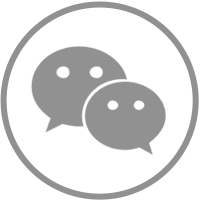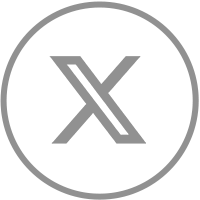作家遲子建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小說的寫作與閱讀時說:「福克納有兩類作品,像《喧嘩與騷動》這類我不喜歡,這種小說看起來很吃力,智力跟不上;但我看《我彌留之際》和《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等一些短篇,就覺得寫得很單純、很透亮,晶瑩剔透……但他的名著倒不一定能讀下去。」
這段話,讓筆者頓生一種終於尋回自信的釋然解脫。想當年讀《喧嘩與騷動》,可以說屢戰屢敗,拿起又放下,邊讀邊忘。如此名著,卻久久體會不到妙處,自己的悟性實在是太低了。原來,像遲子建這樣聰明的作家,也感到「智力跟不上」,那麼咱也就完全沒必要再為難自己。
而像《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既淺又深,文筆淺白好懂,力量卻直徹心扉,久久難忘。讀遲子建的小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能明顯感受到她從福克納作品中汲取的靈感。
「名著」這兩個字,不知是誰先發明的。好像如來神掌變化的五行山,稍不留神就像孫猴子一樣,被壓在底下,喘氣不得。讀《喧嘩與騷動》,讀《尤利西斯》《百年孤獨》,也是這種感覺。
老舍也曾經說過:「這類書是這樣的:名氣挺大,念過的人總不肯說它壞,沒念過的人老怪害羞地說將要念。譬如說《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羅馬的悲劇,辛克萊(Sinclair Lewis)的小說……我不害羞,永遠不說將要念。」「不懂的放下,使我糊塗的放下,沒趣味的放下,不客氣。」
其實,每個人的學識積累、興趣愛好,都不相同。而小說的文化地域背景、作者的寫作技巧和敘事風格,更是千差萬別。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沒個統一的標準。老舍、遲子建尚且有不懂的時候,咱們何必跟「名著」假裝客氣呢?



評論
查看更多評論>>
加載中……

熱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