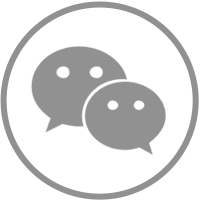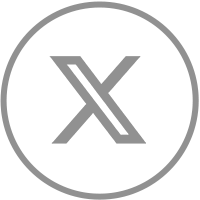俄烏衝突與特朗普當選都是本世紀最重要的黑天鵝事件,對歐洲造成空前的威脅和挑戰。以至法國主流媒體都不約而同一而再地使用「俄羅斯─美國軸心」一詞。「軸心」在西方現代歷史上一向用於有嚴重威脅的敵對勢力。只是今天的歐洲儘管面臨俄羅斯和美國雙重夾擊,但中歐關係並沒有因此而改善。
2019年歐盟把中國定性為系統性競爭對手,2023年和中國有密切經濟關係的德國也步其後塵。今年荷蘭則以強行接管安世半導體的行動證明自己的立場。當前歐盟面臨如此外部困境也不改變對華政策,中歐關係難以有質的突破和改變。這說明中歐關係要想有破冰點,只能寄希望於未來歐洲自身的變局。
進入21世紀以來,右翼政治勢力在西方開始取得更大話語權。最早的標誌性事件是2002年法國右翼政黨領導人勒龐歷史性的進入總統大選第二輪,可謂21世紀的先聲。直到今天右翼政治力量在歐盟27國中的9國執政、特朗普則兩度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由於右翼政治勢力獲得越來越廣泛的民眾支持,在現行西方民主體制下,整個歐盟右翼化已經難以避免。特別是最重要的法國和德國,右翼政黨的支持率都高居第一。右翼政黨執政能成為中歐關係破冰的原因主要有四個:
一是右翼政黨認為它的首要敵人和威脅是外來移民、主張多元主義消解民族特性的政治精英和放棄國家主權的全球主義者。相應的,他們執政首要的目標是恢復國家主權、強化本民族文化特性、驅逐外來移民。
這可從特朗普執政後的表現得以印證:他大量退出國際組織,以擺脫對美國的影響。同時禁止非洲和中東多個國家移民進入,嚴厲打擊非法移民,以維持白人的主導地位。同時實行單邊主義,極力反對全球化。當然國內打擊政治反對派和不認同他的媒體更是比比皆是。
在這種理念下,從特朗普的政策造成的具體效果來看,即使中美戰略博弈的結構性因素都在,但中國不但不是美國唯一的打擊對象,連最重要的對象都算不上。比如它傾向俄羅斯的立場對歐盟安全造成很大的損害,但和中國只是經濟爭端。同樣是採購俄羅斯石油,美國只制裁準盟友印度,但卻對中國只停留在口頭要求上。
二是右翼政黨不認可西方「最新」的價值觀,認為這是導致今天西方問題的根源。比如以人權為名接納大量難民,以自由之名任其在歐洲隨意流動,以民主為名給予他們投票權,並進而影響西方政治。
價值觀是過去歐美和中國發生衝突的主要領域。價值觀和經濟利益不同,無法妥協。以前歐美認為中國的成功已經對它們的價值觀形成替代、構成挑戰。這是歐洲把中國視為系統性對手的主要原因。右翼政黨執政則消除了東西方最主要而且無法妥協的衝突點。
特朗普迄今為止的兩個任期中,中美雙方從來沒有在價值觀上發生過衝突。中美對抗都只是在貿易戰、科技戰、人才戰、關鍵原材料等領域。所以特朗普時代,中美之間不管對抗得多麼激烈,往往可以很快達成妥協。
三是右翼政黨基本上都不是全球主義者,不願意捲入全球事務中,認為代價又高又沒有收益。放到國際現實中就是不干預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干預他國內政,也是東西方對立和衝突的一個根源。
像特朗普不僅不願意捲入外部衝突,甚至連對外援助都放棄。他再度執政當天就暫停所有對外援助90天,四天後乾脆直接下令立即暫停絕大多數對外援助項目。一個月後就決定砍掉美國國際開發署90%的對外援助項目,國際開發署總部也被關閉。國際開發署是冷戰時成立的,它以人道主義為名、宣揚美國的價值觀並配合美國地緣政治利益,通過附加各種條件的援助來干預發展中國家的內政。這包括對反中亂港勢力的支持。
這同樣可以理解,何以特朗普再次當選後,急於結束俄烏衝突,以讓美國脫身。
四是右翼政黨注重具體的利益,因此它們往往更加務實,反而能正視國內、國外存在的問題。比如移民問題和帶來的各種影響,左翼政黨都避而不談。對俄烏衝突,它們認為軍事手段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再打下去也只是個無底洞。但左翼政黨卻要爭取最後正義的勝利。像台灣問題,特朗普就能一針見血的指出,「台灣這麼小,離美國這麼遠。中國這麼強大,台灣又離大陸這麼近。」但這樣實事求是的話政黨是說不出口的。它們只會強調所謂的民主、自身的道義諸如此類。特朗普則簡單乾脆:讓台灣投資美國、台積電去設廠、強迫台灣大量採購武器。先把風險轉為收益。至於歐洲的右翼政黨,更是連對台灣多看一眼都不會。
正是由於右翼政黨的務實性,它們往往能處理好和各大國的關係。比如匈牙利作為西方眼裏的右翼政府,它能和中國、俄羅斯、美國都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才是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相反今天的歐盟則和中俄美關係都緊張。
此外,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於注重利益的右翼政黨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它們同樣希望以經濟成功來證明自己的執政能力和政治理念。
因此,如果日益獲得歐洲民意支持的右翼在歐洲、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執政,對中歐關係來說未必不是新的契機。此時的歐洲既不會視中國為威脅,也不會在價值觀上對立,更不會阻撓中國統一,而是追求合作共贏。到那時中歐才會重返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