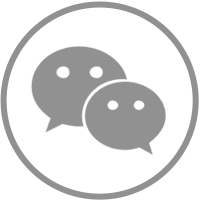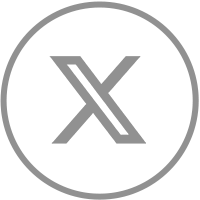過年貼門神是中華民族的古老民俗。有人考證,最早的門神,不是人,卻是虎,其依據就是《周禮》中的一個記載:「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這個說法是否靠譜,我不敢妄斷。不過,有確鑿史料認定的,最早以人的形貌司職門神的,是炎黃時期的神荼和郁壘。相傳這兩位大將能發現惡鬼並將其降伏,所以炎黃子孫們便將他倆尊為最早的門神,守護家門。
到了唐代,神荼郁壘「下崗」了,門神被換成了唐朝的開國大將秦瓊和尉遲恭。這次換崗源於一個傳說,據說唐太宗一度常做噩夢,聞鬼叫而心驚。秦瓊和尉遲恭聞之,每晚全副披掛,在門外徹夜守衛。不過數日,太宗噩夢全消,遂大讚二位將軍「真是門神」。可又覺得他倆白天當值,晚上守夜,太過辛苦,便命畫師畫了秦瓊和尉遲恭的肖像,貼於門上,替代他們守夜。由此,這一皇家欽定的做法廣布於民間,遂使他倆成為佔位時間最長、名聲最響、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對門神。
門神的畫像被尊奉為全民的神祇,應歸功於春節期間家家必不可少的年畫。不論是皇家宮殿還是貧民草舍,過年時總要貼上一對門神,不只為了營造喜慶氛圍,更是為了鎮宅驅鬼,就如同《白毛女》裏的貧家女喜兒唱的那幾句唱詞:「門神門神騎紅馬,貼在門上守住家,門神門神扛大刀,大鬼小鬼進不來。」「騎紅馬」的門神,我從來沒有見過。不過,我倒很想在農曆丙午馬年(二○二六年)到來之際,能見識一下「騎紅馬」的門神,那才叫歲時應景呢。
門神的形象,本應是每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文化記憶。然而,在我的成長歷程中,卻留下了一段記憶的空白。我是在城市長大的,在記事的年齡段,又趕上大破「四舊」的非常時期,自然沒機會見識門神的「尊容」。我最早見到門神,是在天津楊柳青年畫社的外銷部裏,各式門神,大小不一,色彩各異,琳琅滿目。那已經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已進報館當了記者。因為媒體採訪的關係,我與當時的畫社社長李志強先生成了朋友,才得以經常去觀賞精美的楊柳青年畫,娃娃畫、戲出畫、仕女畫、道釋畫,等等。志強兄還送給我一本當時印的介紹楊柳青年畫的圖錄,第一頁是名人題字,第二第三兩頁,就是一對大門神:尉遲恭和秦瓊,一個面黑虬髯,面目猙獰;一個面白長髯,眉目清秀。這對門神我在展銷廳見到過,標價不菲,可見是非常珍貴的。志強兄介紹說,這對大門神是清代時的老闆印的,據說,當年是進貢給慈禧太后在清宮大門上貼的。好多年都沒再印,這次重印出來,作為楊柳青年畫的代表作,就給排在圖錄的最前頭了。
大概是一九八六年吧,我去陝西鳳翔採訪震驚考古界的秦公一號大墓的發掘實況。在這片古老的鄉土,我第一次見識了家家戶戶貼門神的景象——彼時的季節雖已過了新春喜慶的高潮時段,但是各家門神的殘跡依舊隨處可見。這裏的門神,刻畫簡單,單色平塗,形象質樸,表情誇張,是典型的鳳翔年畫的風格,與楊柳青的門神差別明顯。可巧,我在鳳翔駐留期間,正趕上當地文化部門舉辦一次民間藝術的調研活動,而在我所住的賓館裏,又無意中與主其事者有緣相識。如此一來,我竟被邀請作為外地媒體的記者,全程參與了這次對鳳翔民間藝術的考察之旅。在有名的鳳翔年畫主產地南肖里村,我觀賞了當地畫師的製作流程,也見到了當地世代傳承的年畫家族的傳人,還與他們交流了天津楊柳青年畫的不同製作方法。那位老畫師發現我還算個內行,非常興奮,特意拿出一塊老畫板給我看,那是一個蒼鷹的刻版,年深日久,已經殘損斑駁了。我悄聲問畫師:「你家有沒有門神畫?」他說當然有啦,可是現在沒存貨了:「門神是過年貼的,我們都是過年前才印,早就讓鄉黨買光了,明年的還沒開印呢。」可能是我露出了一絲憾意吧,老畫師也有所察覺,似乎略有歉意,臨行前,就找出一張用那老版印製的蒼鷹圖,執意要讓我帶走,並且熱情相邀:「您到明年過年時候再來,我把門神給你留着……」我被鳳翔人的熱情深深感動,同時也對鳳翔年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回到天津,發奮研讀鳳翔年畫的文獻資料,並與楊柳青年畫作了比較,用功經年,寫出了一篇萬字長文《楊柳青與西北風——楊柳青年畫與鳳翔年畫的比較研究》。這篇論文在首屆中國木版年畫研討會上(一九九一年)首次宣讀。我並不奢望鳳翔的那位老畫師會看到我的論文,但是,我的這份「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心意,已得到了一次酣暢的宣洩。
一九九三年一月,我南下深圳。剛到嶺南的那段日子,時常接待來自天津的各方友人,其中就包括楊柳青畫社的一班老友,來得比較勤的是王洪增、于錦聲、于晉鯉……他們有時是來辦展,有時是來「走穴」。有一次,他們北歸之前來我家小聚,帶來一個大畫盒。洪增兄悄聲對我說:「這件東西,本來是人家訂的。誰知帶來以後,人家看中了別的,這件不要了。我覺着挺沉的,再背回去也犯不着,就送給你吧,你懂行,留給你肯定有用——」他小心翼翼地打開木製的畫盒,我一看,不禁喜出望外:那是一對大門神,就跟我當年在畫冊上看到的一模一樣。我無法抑制自己的興奮之情,杯酒下肚,對他們幾位動情地言道:「你們不會想到我是多麼喜歡這對門神!你們想想,我們是舉家南下,來到嶺南,無親無故,連話都聽不懂,想念家鄉,想念親人和朋友,無法排解呀!有了這對門神,就好像請來了兩位天津老鄉,每到年節就來陪陪我們,解解鄉愁啊……」我無法拒絕這份來自故鄉的厚贈——從此,這對門神成為我在深圳家中,每至春節必須張掛的「圖騰」,這一掛就是二十多年。
唯一遺憾的是,這對門神只能掛在我們為它專門留出的一面白牆上,卻無法依照他們本來的身份,掛到我家的門上。門神門神,不能上門,總不能算是「諸神歸位」吧?然而,現代都市的住房,均已變成一個個「水泥格子間」,以往那種對開的大門已經悄無聲息地退出了當今都市人的生活;而大規模的新農村建設,勢必會讓古老的鄉土中國,迅速轉向城市化,農家小院的大門會不會也被單元門所取代呢?門之不存,神將焉附?每思至此,心底不禁又泛起一縷淡淡的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