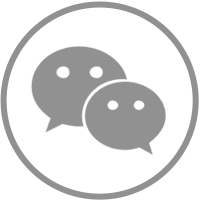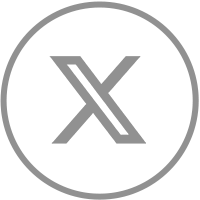居京三十多年,我從未踏足過地壇,卻在史鐵生的文字裏,無數次走進這方園子。史鐵生在地壇十五年間關於母親、關於苦難、關於命運與活着的思考,讓我們在地壇以外形形色色的人生中,一直在體悟。
新年去拜訪恩師,恩師的府邸恰好在地壇公園對面。傍晚從恩師家出來,就奔了園子。冬日的晚霞透過高樓,投射在朱紅宮牆上。我想趕在天光落盡之前,去看看「鐵生的樹」,從南門按導航往園子的北邊,沿途匆匆辨看一棵棵被認養樹木上有趣的「名字」:「葉問與李小龍」「生生不息」「小瑤的發財樹」……
我要找的兩棵樹,一棵叫「鐵生的朋友余華」,一棵叫「余華的朋友鐵生」,都是槐樹,位於地壇北天門的西牆外。關於兩棵樹,有另外一段佳話。與我常去的天壇公園之端正大氣不同,地壇更有「大地」的親和,是個有溫度的地方。這座古老的園子現今又被賦予了越來越多的標籤和越來越多的想像,成為人們的情感投射之地。地壇不再只是一座園林一個地名,更像一個精神符號、文化符號了。
我與「余華」「鐵生」兩棵樹拍完照,天色已晚,沿着園子西邊的齋宮走,突然覺得沉入了史鐵生的地壇──「十五年前的一個下午,我搖着輪椅進入園中,它為一個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那時,太陽循着亙古不變的路途正越來越大,也越紅。在滿園瀰漫的沉靜光芒中,一個人更容易看到時間,並看見自己的身影。」
「自從那個下午我無意中進了這園子,就再沒長久地離開過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圖。」
如今,距《我與地壇》發表的一九九一年也已經三十五年了,我在史鐵生初次走進地壇五十年後的這個傍晚,第一次來到這裏。
我並不想刻意去尋覓史鐵生在園中的足跡,地壇的每一棵樹下他都去過:「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過我的車輪印。無論是什麼季節,什麼天氣,什麼時間,我都在這園子裏呆過。」當年的地壇「滿園子都是草木競相生長弄出的響動,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在人口密聚的城市裏,有這樣一個寧靜的去處,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是可以逃避一個世界的另一個世界」。而今園子不再荒蕪,卻多了一種別樣的氣質。老北京的紅牆古樹、園子都有,但還有一種非碧瓦朱牆,非銀杏蒼柏,非皇家底蘊……以外的、無形無色無味卻有感的氣息。儘管第一次來,但這種氣息一下子就把我籠住了。我只覺得這園子有一種熨帖心境的溫厚。
「多年來我頭一次意識到,這園中不單是處處都有過我的車轍,有過我的車轍的地方也都有過母親的腳印。」──我一下子想到了史鐵生的這句話。
我親愛的母親走了近兩個月,我每天都在想她。每每音容笑貌浮現腦海,或者望見一個場景,看到一段文字,甚至與母親毫無瓜葛的場景,都會潸然淚下。母親在北京治療期間,我們帶她去了天壇、陶然亭、綠堤公園。五月的北京,繁花盛開,綠樹茵濃。我們推着母親在花間樹下走,母親說:「真好啊!斑鳩那時每天在卧室窗外咕咕叫着探頭探腦……」我更願意想起母親的笑容,就是在她去世前十來天,母親清醒時看見我們依然會朝我們笑,眼神亮亮的,充滿歡喜充滿慈愛……前些天我在想斑鳩為什麼不來窗前叫了,結果第二天牠又來了。只是窗內,已經沒有了我的母親。
地壇的園子,也充滿着一樣一樣的對母親的懷念:「搖着輪椅在園中慢慢走,又是霧罩的清晨,又是驕陽高懸的白晝,我只想着一件事:母親已經不在了。在老柏樹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頹牆邊停下,又是處處蟲鳴的午後,又是鳥兒歸巢的傍晚,我心裏只默念着一句話:可是母親已經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沒,坐起來,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壇上落滿黑暗然後再漸漸浮起月光,心裏才有點明白,母親不能再來這園中找我了。」
晚霞的餘光將地壇的一切都襯成剪影。我在地壇感受着「我與地壇」、「我」與母親,感受着那些發乎地壇、直抵心底的情感。有些情感,只屬於此地;有些情感,超越此地;有些情感,在此地共鳴、迴盪、隔空交響。
冬天的風正從樹林裏穿過。四百多年的老園,這樣的風一次次翻動起安詳的落葉,生命一代一代地走過。在浩瀚的宇宙中,很多生命、很多我們以為的驚天動地,不過輕輕一掠,了無蹤影。但有些生命的存在,只有我們知道,「天空不曾留下翅膀的痕跡,而他/她已經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