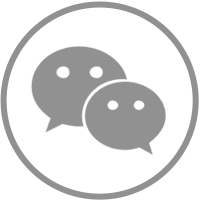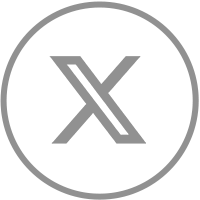我站在博物館的玻璃櫃前,左右兩側,是兩個朝代的呼吸。左邊,是一隻宋代的素色茶盞,天青的釉色像是從一場清晨的薄霧裏凝結出來的,沒有絲毫火氣,只有溫潤的、內斂的光澤。碗身找不見一筆多餘的描畫,線條簡淨得如同山脊的剪影。右邊,是一件清代的粉彩大瓶,瓶身上,牡丹、錦雞、雲紋、回字,一層疊着一層,用金線勾了邊,用礬紅點了蕊,熱鬧得彷彿能聽見集市裏的喧嚷。瓷是冷的,那份鋪天蓋地的華麗,卻帶着一股暖烘烘的、屬於人間煙火的體溫。
這份溫熱,讓我忽然想起清人筆記裏的一則軼事,說的是康熙年間,廣州十三行的買辦,為宮裏採辦一批自鳴鐘。那鐘運到宮中,不僅能報時,更有活動的小人兒,到點便從鏤花的金門裏轉出來,敲擊音樂。太后看了喜歡,卻嫌那小人兒衣裳是西洋式樣,吩咐工匠:「給他們換上咱們的綾羅,臉孔也畫得喜慶些。」於是,琺瑯彩繪的匠人們,便在那方寸之間,用工筆細細描上團花紋的馬褂,點了朱唇與笑靨。物質的豐盈,讓審美有了「添一點,再添一點」的底氣與從容,彷彿不多,便不足以顯其盛,不繁,便不足以表其榮。那是一種飽滿的、無需節制的誠意,是堆疊出來的盛世圖景。
我的思緒,卻不由自主地被左邊那片清寂的青色拉了過去。那青色背後,是另一番天地了。我想起蘇軾。他晚年被貶至海南,那真是國家的邊緣了。史料裏說,海南當時「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他給朋友的信中,卻還能苦中作樂地描述發現生蠔的歡喜,琢磨如何烹食。他的生活,是被迫的「樸素」,是物質層面的艱困。然而,就在這樣的境地裏,他寫出了「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這樣的句子。他用的器物,想必也是粗陋的。但那份「本澄清」的觀照,是否正因剝離了諸多外物的紛擾,才愈發逼近生命的本真?
宋人便是將這種物質條件,或曰科技形態的局限,淬鍊成了一種主動的選擇與至高境界。他們的窰工,並非燒不出繁複的顏色。那是一種在當時的技術條件物質條件下的「窮而後工」。沒有遠方珍稀的礦料,便將腳下的土與火用到極致;物流艱難,器型便多為實用,線條因之純粹;農業在地,色彩便取自風霜雨露,青是雨過天青,白是月下凝脂。他們的「雅」,並非不食人間煙火,而恰恰是將人間煙火——那有限的、樸素的煙火——提煉出了神韻。宋朝的審美,是在窄門裏走出寬闊,在匱乏中生出豐饒的精神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