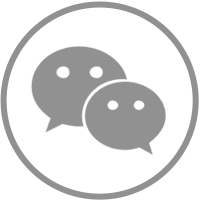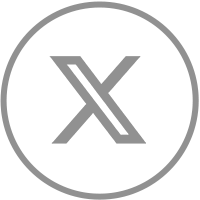歷史上,美國人很忌諱其他人用「大美帝國」來描述美國。他們強調美國是一個通過推翻英國的殖民統治而成立的國家,因此作為一個推翻殖民統治的國家,美國本質上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而美國更一直在世界上高舉反對殖民主義的旗幟,並在二戰後初期發揮了重要的瓦解歐洲國家的殖民帝國的作用(當然在冷戰發生後美國卻成為歐洲國家的殘餘殖民帝國的守護者)。然而,最近幾十年來,美國人對「大美帝國」的標籤不但不抗拒,更覺得有一點點的自豪感。美國的專家學者更發表了海量的關於「大美帝國」的書籍和文章。
有趣的是,縱使美國人願意承認美國是一個龐大的「帝國」,但他們卻辯稱「大美帝國」與歐洲國家的帝國有着本質上的差別,主要原因是美國沒有通過武力侵略在其他地方建立殖民地、奴役當地人民和掠奪他們的資源。他們認為,「大美帝國」是由其他願意參加的國家和地區所組成。這些參與者期望作為「大美帝國」的成員能夠得到諸般好處,特別在經濟利益和安全保證上,並且不會被美國壓迫和搶掠。因此,「大美帝國」是一個「邀請型帝國」(empire by invitation),參與者是應美國的邀請、心悅誠服而來的。
「大美帝國」與殖民無異
這種對「大美帝國」的描述和認知顯然是對歷史肆意的扭曲、美化和譏諷,目的是要肯定所謂「美國例外論」,即美國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國家,「大美帝國」的宗旨是要按照上帝的意旨去改變和造福人類,而這個上帝的意旨就是美國要履行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
然而,這種美化和歌頌「大美帝國」的描述明顯與歷史事實不符。真實情況是,在二戰以前,在構建其帝國的過程中,美國的行為和方法與歐洲國家比如英國、法國和西班牙並無二致,都是以軍事征服、土地掠奪和建立殖民地或者類殖民地比如保護地(protectorate)作為主要手段。那些歐洲帝國也與美國一樣用某種道德理想來包裝或掩蓋它們的惡行,比如英國人的「白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和法國人的「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
美國於1776年立國後,其領導人便不斷使用武力和殺戮對外開拓疆土,並成功讓美國的領土不斷擴張。當然,部分新增疆土從英國、法國、西班牙和俄羅斯購買而來,但美國的武力仍然是其他國家「願意」向美國出售領土的重要後盾。誠然,美國在開疆闢土時未竟全功,比如未能吞併加拿大和墨西哥,但其最終所獲得的領土已經是相當廣袤。
倫敦大學榮譽教授維克多·布爾默─托馬斯(Victor Bulmer-Thomas)在其《帝國的衰落》(Empire in Retreat)一書中講述美國如同其他歐洲國家帝國一樣都是依仗武力征服來建立一個「領土帝國」(territorial empire),即是通過取得領土、建立殖民地或其他地位與制度安排、進行直接或間接管治而掠奪其資源和奴役其人民。舊式帝國主義的最大特點是以霸佔土地為帝國的要務,而領土爭奪又往往是不同帝國之間的戰爭和衝突的導火線。
《帝國的衰落》一書中對美國立國後的領土擴張有這樣的描述:在1775年獨立戰爭爆發之前,開國元勳們對帝國主義本身的概念並無異議。美國獨立後便在美洲大陸大肆擴張,並導致其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舊西北領地讓美國聯邦政府首次體驗了殖民統治。……『昭昭天命』是一種意識形態化的、種族主義的、準宗教式的理論,它支撐着美國對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北美所有土地的主權主張。」之後,「美國在中美洲的帝國控制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區都更為全面。」「1898年美西戰爭後,古巴、波多黎各、關島和菲律賓成為美國殖民地。其中兩處領土(波多黎各和維京群島)成為美國殖民地,另外三處——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國和海地——則透過一系列類似歐洲帝國主義的手段進行控制。」此外,美國又通過推翻夏威夷王國的女王而把夏威夷納入美國的領土。
二次大戰後,由於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去殖化運動風起雲湧,要保留原來的殖民地或建立新殖民地頗為困難,因此美國便不得不改用其他方法——主要是經濟、政治和外交手段——來建構「大美帝國」,當然軍事威嚇和可能的軍事介入依然在背後發揮關鍵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以此之故,縱然二戰後歐洲國家的殖民帝國因為其殖民地紛紛獨立而轟然倒塌,但「大美帝國」卻依舊屹立不倒,而一些歐洲國家的前殖民地甚至被納入其中。可以說,二戰後的「大美帝國」是一種「新型」的帝國主義,與過去的帝國主義在掠奪和壓迫的本質上雖然相同,但在形式上卻有異。
以「規則」為名掠奪資源
布爾默─托馬斯指出:二戰後,美國建立的「帝國」,是建基在美國制定的規則之上,並以美國控制的機構為支撐。這些結構包括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及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其賴以存在的價值觀隨後由一系列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比如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美國之音(VOA)、政黨、跨國公司、媒體、教育與文化機構、宗教組織和美元傳播到海外。它並不依賴於領土擴張,因此,在理想情況下,美國無需干預他國事務。這些機構將確保其他國家遵守規則,而國家行為的道德力量將鼓勵它們這樣做。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美國也會對其他國家進行干預,包括介入其選舉過程。美國的干預採取了多種形式。有時是直接的,涉及美國軍隊;有時則利用代理人;很多時候,儘管當時並未被廣泛意識到,但干預是秘密的,即使是按照美國法律也並非總是合法的。這種干預發生在「大美帝國」活動的各個地區——西歐、亞太地區、中東、非洲和美洲。對此,大衛·A·萊克(David A. Lake)在其《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一書中有詳細描述。
美國所建構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美國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航道暢通、維持地區和平、信息流通系統)、美國對外開放的市場、美元作為最重要的國際貨幣、美國適度容許或容忍其他國家和地區搞點貿易和產業保護主義、美國的大量對外投資與援助都是長期以來支撐「大美帝國」的工具。也就是說,美國除了利用其「帝國」對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剝削和掠奪外,同時也為它們提供一些對其的發展和福祉有幫助的事,不完全是只取不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大美帝國」的國際「認受性」。
此外,一般人比較忽略的是,數以百計的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和設施也是「大美帝國」的重要支柱,而那些基地和設施在本質上其實也是美國在海外的「殖民地」,亦彰顯了武力在建構和維護美帝國主義中的關鍵性。美國大學人類學教授大衛·瓦恩(David Vine)在其著作《戰爭中的美國》(The United States of War)中指出,歷代美國領導人透過建構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外軍事基地網絡,將美國鎖定在一個自我延續的永久戰爭體系中。「軍事基地將有助於維護聯盟關係,保障美國企業的盈利機會,並獲取自然資源,例如對資本主義日常運作和軍隊本身至關重要的石油供應。」「大量的海外軍事基地成為『美國帝國』控制的主要機制,使其控制的領土與實際佔領的土地面積嚴重不成比例。軍事基地體系代表着美國實力的急劇擴張,也是美國維持戰後霸權的重要途徑。」
綜上所述,在二戰前,「大美帝國」在形式和本質上與歐洲國家的帝國並無二致。在二戰後,儘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即不以控制疆土為基礎,但在控制和掠奪資源和財富為目的上,「大美帝國」與歐洲國家的帝國在本質上並無不同。
「炮艦外交」加速霸權崩塌
然而,近年來,隨着美國的國力下降、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再起、一些區域性大國的冒起和全球南方的興起,美國感到極度焦慮和不安,一方面覺得「大美帝國」面對嚴峻挑戰,另方面則發現維持其「新型」帝國主義的成本越來越高、但收益卻越來越少。簡單來說,美國難以像過去般向「大美帝國」的成員提供一些好處和利益以換取它們向美國歸順,而美國不但越來越不願意遵守其制定的國際規則,反而粗暴摧毀其構建的「自由國際秩序」。
為了阻止「大美帝國」走向分崩離析,美國最近明顯揭開其過去的「懷柔政策」和「與人為善」的面紗,暴露其本來面目,積極利用其手上仍然龐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尤其是前者——對其他國家進行明目張膽的搶掠和侵略。特朗普政府威脅用武力奪取加拿大、格陵蘭和巴拿馬運河,並悍然踐踏國際法、對委內瑞拉動武和擄走其總統與其夫人,目的是要控制和奪取該國的石油。美國又為了自身經濟利益,不惜以關稅和其他保護主義手段對全世界發動貿易戰,並對包括其盟友在內的國家進行恐嚇和勒索。這種試圖通過武力侵略和經濟脅迫來擴張領土、搶奪資源、逼迫他國就範和爭取美國利益的手法,是美國重回舊帝國主義特別是領土和資源帝國主義老路的明顯跡象。
更令人唏噓嘆息的,是美國不再如舊式帝國主義般用道德理據或崇高理想來「合理化」其霸凌行為,反而赤裸裸地訴諸自身狹隘利益和不對等的交易主義(transactionism)。不過,姑無論其最終能否成功,但美國重回舊式帝國主義的姿態和行為已經昭然若揭。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學教授阿爾弗雷德·麥考伊(Alfred W. McCoy)在2026年1月13日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是一個『衰落的帝國』,其衰落遵循着一種可預見的模式:在海外推行軍國主義,在國內陷入政治動盪,同時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實力和影響力也在不斷下降。」他預言,「美國帝國」還會延續一二十年,直到美國國力最終不斷流失。在衰落過程中,美國會向海外派遣軍隊,並認為某種形式的軍事干預能夠讓美國重新奪回正在從手中溜走的全球權力。他指責美國正在重蹈其他帝國滅亡的覆轍,走上炮艦外交的道路。
毫無疑問,在世界走向多極化、民族主義熾烈、中國崛起成為維護世界和平和公義的中流砥柱的今天,國力不斷下滑和在國際上愈趨孤立和失道寡助的美國,要繼續維護「大美帝國」不啻是緣木求魚,勉強為之只會加快帝國的崩塌和美國國內的鬥爭和動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