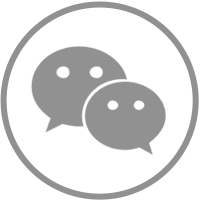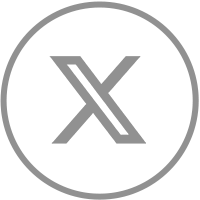干支輪迴,又逢馬年。當生肖文化以它獨有方式將「馬」推至舞台中央時,我們從中審視的不僅是一種生靈,更是歷史長卷中一道深刻而複雜的文明拓片。馬,這個自石器時代便與人類命運交織的物種,其形象早已超越生物範疇,成為華夏文明乃至人類歷史中一個內涵豐沛的象徵符號。
漢代桓寬在《鹽鐵論》中曾這樣斷言:「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其金石擲地之聲,穿透兩千年塵囂,直指馬在華夏文明譜系中的樞軸之位。從冷兵器時代的戰馬嘶鳴,到絲綢之路上的駝馬並駕,再到現代語境下的精神圖騰,馬的蹄聲始終在文明的殿堂裏迴盪,既踏出了金戈鐵馬的雄壯,也叩問着速度與馴服背後的文明悖論。
馬之為用,首在力與速的物性昇華,堪稱文明拓疆之基石。在冷兵器時代,騎兵乃戰爭之王,馬甚至可以去定義國家的武力與疆域版圖。武王伐紂,「駟騵彭彭」,周人以車馬之利克商;秦漢之際,匈奴「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其強大騎兵迫使中原築起萬里長城;春秋戰國時期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絕非衣冠之變,而是深刻的軍事與社會革命,馬成了趙國變法圖強的鋒刃;漢武帝為求大宛汗血寶馬,不惜傾國之力遠征,其執念的背後,是對戰略資源「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的極致渴望。因為馬的良莠,直接牽動着帝國安危與興衰命脈。更觀蒙古大軍依仗耐力超群的蒙古馬,如旋風般席捲歐亞,馬背不僅承載戰士,更馱起一個空前遼闊的帝國疆域。馬以其血肉之軀,化作冷兵器時代最為關鍵的軍事裝備,成為力量投射與空間征服的核心載體。
由戰爭動脈而經濟血脈,馬匹進而成為文明交流的鮮活媒介與絲路繁華的躍動音符。絲綢之路,這條連接東西方的文明大動脈,其繁盛離不開駝隊,亦仰仗馬幫。商隊鈴聲與馬蹄聲交錯,貨物與思想也隨之流轉。唐代設立完備的驛傳系統,「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駿馬奔馳,保障了政令暢通與物流高效。馬匹本身還是重要貿易品與外交禮器,類似昭陵六駿所折射的良馬崇拜,抑或唐玄宗為求吐蕃良馬而進行的金帛易駿交易,馬不僅拉近了地理距離,更在貿易、使節往來、宗教傳播中,編織起一張跨越民族與文化的動態交流網絡,促成盛唐胡馬入華風的融合氣象。
超越實用藩籬,馬更躍入華夏精神的蒼穹,成為文化意象與人格象徵的璀璨星辰。在文學疆域,它既是《詩經》「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的雄渾背景,亦是曹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壯志載體,更是杜甫「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的豪情寄託。尤其是羅貫中筆下的三國風雲,更加淋漓盡致地展現了馬在歷史關鍵時刻的非凡角色。呂布胯下的赤兔馬,「渾身上下,火炭般赤,無半根雜毛;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其所謂「人中呂布,馬中赤兔」,幾近成為武力巔峰的象徵。此馬先隨呂布橫掃中原,後歸關羽,助其斬顏良、誅文丑,過五關、斬六將,成就武聖威名。一匹馬連接兩位絕世武將的命運,其神駿腳力直接參與塑造了歷史格局。而劉備之的盧馬,雖背負妨主之名,卻在檀溪性命攸關的驚天一躍中,馱着劉備脫離絕境、化凶為吉,改寫了蜀漢創始人的命運軌跡。
當歷史浪潮奔湧至工業革命的拐點,蒸汽機的轟鳴終於漸次掩蓋了清脆的馬蹄之聲。馬在傳統的交通、軍事、農耕中的主導地位不可逆轉地式微,淡出了實用的台前。然而,其文明印記並未就此湮沒,駿馬的形象從沙場悍將悄然轉型為文化與心靈的使者。其忠誠、勇毅、耐勞的品性,更與儒家推崇的君子之德相契合,成為人格砥礪的鏡像坐標。在中國文化的譜系中,馬被賦予了乾象、陽畜的哲學意涵,象徵着天行健的剛健精神與君子自強不息的韌性品格。伯樂相馬的典故,早已超越畜牧學,成為對識才之智與用才之道的永恆隱喻。韓愈「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的喟嘆,道盡了人才與機遇的千古命題。杜甫詠馬「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讚譽的是其俊逸神采與不凡氣骨;徐悲鴻筆下奔放的駿馬,更是民族危亡之際奮起精神的激昂寫照。在西方,希臘神話中那匹長有雙翼的佩伽索斯馬是靈感與詩性的化身;中世紀騎士文學中,馬同樣也是忠誠、榮譽與高貴情操的夥伴。此等文化建構,使馬從役畜一躍而蛻變為蘊藉深厚的文化靈獸,在各個族群的集體心理中刻下深深烙印。馬,已然成為一種跨越文明的精神符碼,凝結着人類對力量、自由、忠誠與超越的共同想像,尤其像「馬到成功」「龍馬精神」等成語的鮮活運用,愈益昭示着馬文化奔騰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內核,依然在激勵着現代人奮發前行。
我們值新春再聞馬歲鐘聲之際來說馬,絕非僅作生肖應景,而是透過這一獨特視角,試圖進行一次文明肌理的縱向掃描。從金戈鐵馬到文化駿驥,馬的形象流變,足以讓世人深切地品味出文明進程中力量與倫理、征服與共生、利用與敬惜的永恆張力。那穿越歷史煙塵的聲聲蹄響,不僅是過往的回音,更是對未來的叩問:在人類駕馭自然能力空前強大的今天,我們能否以更為清明與仁厚的智慧,處理好發展與倫理、權力與責任的關係?或許,馬年沉思的真正價值,就在於讓我們在聆聽那漸行漸遠的歷史蹄聲時,獲得一份關於文明前路的深刻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