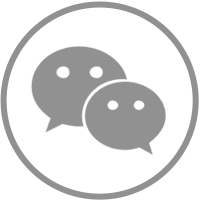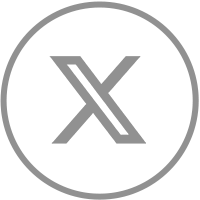每當新年或新學期來臨,總會有不少人將學習外語設為目標。通曉一種外國語言,可以令人腦筋活絡,視角新穎,靈感與之俱來,世界因之變容。世人學外語,原因和目的五花八門。比如我學英語和法語,是因為不學就無法畢業;學日語,原本只是想聽懂日語歌曲;學韓語則純因好奇,想知道那些像甜甜圈和麵包棍的符號是什麼意思(學後方知,它們只是表音的字母)。後來,我能夠用外語讀寫聽說,外語知識帶來的快樂和力量,遠遠超越了學外語的初衷。
英國作家、《三人同舟》的作者Jerome K. Jerome在自傳中說,想在外國過寧靜的生活,只需掌握當地語言的二十個動詞、一百個名詞、十幾個形容詞和代詞就足矣。確實,如果僅為旅行,何妨學一些日常會話,因為詞彙簡單,也不必糾結語法,鸚鵡學舌,蜻蜓點水,易如反掌。別人還在因為餐館沒有WIFI、連不上谷歌翻譯而人仰馬翻時,你已用當地語言為同行諸君點好了紅茶、咖啡、果汁、礦泉水,然後輕呷一口冰涼的可樂,對四面八方拋來的驚喜和恭維浮起一個甜笑。
若是發奮進學,「洗手間在哪裏」、「啤酒謝謝」這幾把板斧當然不夠。做學問貴在視野寬廣,能夠直接閱讀外語文獻是求學的第一步。研究生時代,我的一位導師通曉七種語言,還鼓勵我多學一門外語,「多多益善!」陳景潤在學生時代學了英語、俄語,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後,為盡快讀到國外論文,又自學德語、法語、日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我必須檢閱外國資料的盡可能的全部總和,消化前人智慧盡可能不缺的全部果實,而後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解答(1+2)這樣的命題。」中學時代在徐遲《哥德巴赫猜想》中讀到這段話,感佩無已。
然而,很多人終生都在與一門外語掙扎,因為用進廢退,若非長住外國或有工作之需,平常使用外語的機會並不多。千辛萬苦背單詞,記三個,忘五個,七零八落。追劇呢,又常被劇情一路吸引,只顧看字幕翻譯。看懂外語肥皂劇並不難,而書籍所含信息更密集、更系統,所以讀外語書更燒腦、更考驗毅力,收穫也會更顯著。掌握基本語法和詞彙後,可以立即攻讀外語原著。劉易斯(C. S. Lewis)十五歲時跟從私人教師Kirkpatrick學古希臘語。第一節課,老師一口氣將《伊利亞特》一百餘行譯為英語,僅稍加解說。譯畢,丟給劉易斯一本古希臘語詞典,令他溫習方才口授章節,之後揚長而去。起初劉易斯亦步亦趨,很快就能夠理解原著大意。老師又以同樣方式教授德語和意大利語,帶他讀《浮士德》和《神曲》。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吉本在自傳中回憶少年時學拉丁語,先將西塞羅的一篇作品翻譯為法語,擱置數周後,再將法語譯文翻譯回拉丁語,最後將自己的拉丁語翻譯與西塞羅的原文逐句對照。如此,自修外語的同時還精讀了名著。
學生時代,我追慕前賢,學日語未及兩年,就霸王硬上弓,挑戰井上靖獲芥川獎的小說《鬥牛》。每晚在圖書館獨佔一張巨大的原木方桌,「劍拔弩張」,對照劉慕沙的中譯,與枝蔓纏繞的長句作車輪大戰。井上靖是日本老一輩作家,其作品不像村上春樹、夢枕貘等通俗作者的那樣輕巧易讀,但辛苦讀畢,豁然開朗,有登堂入室之感。此後每次回母校,都會去圖書館看望那幾張大木桌,在心中問一聲:「別來無恙?」
學外語也不必帶有任何功利目的,只為求知。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推崇eudaimonia,通常譯為「幸福」或「快樂」,但它並非某種靜止的心理狀態,而是以智力活動──主要是求知、思考──為主體構成的充實、至善的人生。英國作家毛姆的小說《刀鋒》塑造了「人中麟鳳」拉里,他通曉法語和拉丁語,已讀完法國文學的所有重要作品,並開始自學希臘語、心理學,一切都為「獲得知識」。他告訴女友:「你絕對想像不到讀《奧德修紀》的原文多麼令人興奮,彷彿你只要踮起腳、伸出手,就能碰到天上的星星……前一兩個月我讀了斯賓諾莎。我不敢說我已經完全懂得,可是感到非常振奮,就像乘飛機降落在巍峨群山中的一片高原上,四圍萬籟俱寂,空氣非常清新,如佳釀沁人心脾。」
舊時學習外語,連正式課本都沒有。康拉德的母語是波蘭語,二十歲始學英文,用第一次領到的薪水購得《莎士比亞全集》苦讀。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在《遊華記錄:わが留學記》回憶,他一九二八年留學北平,請兩個旗人教他漢語,用的課本竟是《紅樓夢》。如今學外語條件優裕,聲光電設備俱全,但技術手段只提供一時便利,無法替代勤奮和恆心。「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嘗試靜下心來,學好一種外語,將自己的認知圈拓展出新的維度,用不同的語法結構和思維方式觀察人生、談論世故,在大腦中恣意切換聲音、符號、文化背景、異域想像,享受單純的求知過程,由點及面,融會貫通,發憤忘食,樂以忘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