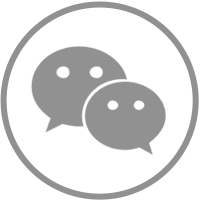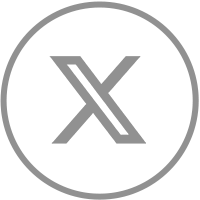美國檔案中早期中國留學生的姓名拼寫不規範,除了使用韋氏音標,還有不少根據方言拼寫。如,「許」拼為Hsu是用了韋氏音標,但「徐」寫作Zee,就類似江浙一帶的發音了。地名同樣如此。除了北京舊稱「Peiping」,南京叫做「Nanking」,九江、江陰、察哈爾的拼法都與今有別。而《民國名人錄》等辭書和網絡資料中對我校校名的譯法也不統一,稱格林奈爾、葛林乃爾、格銳乃耳、葛林如爾、葛林諾爾的都有,有的還和康奈爾大學混為一談。山東博文中學的校史介紹中還有「歌仁乃樂」之稱,雅馴有餘,而信達不足。
鑽故紙堆,搜檢數據庫,瀏覽網頁數月,幸而收穫不少。二十世紀初我校知名中國校友不僅限於之前早知的國民黨元老吳國禎。從政的有李光釗、查良釗,進入銀行業的有黃勤、王祖廉。當大學教授的最多,包括孔繁矞、馮文潛、盧開運、劉紹禹、張杰民、程德諝、趙宗晉等。還有遠東運動會金牌獲得者,外號「飛毛腿」的南開校友郭毓彬,被張作霖以「赤化」罪殺害的北大教授高寶壽(仁山)。
當年校友人才濟濟,在不同領域各領風騷。他們何其有幸,能得風氣之先,遠渡重洋,接受教育,見識世界。但作為跨文化的先驅者和實踐者,他們在二十世紀的風雨中可能也比他人經歷了更多的考驗甚至磨難。由此我也想到一些問題:誰會被後世記住?他們將怎樣被記憶?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歷史中他們會分別以什麼形象出現?除了在學校、工作單位的檔案中留下痕跡,還有什麼途徑保證個人的存在有所記錄,有所傳承呢?



評論
查看更多評論>>
加載中……

熱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