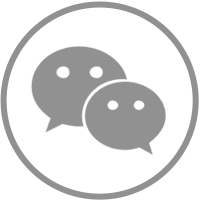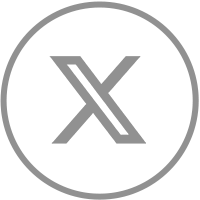我雖然從小近視,聽覺卻超靈敏。在隔壁房間小聲說我的壞話?休想。「聰明」一詞,源自「耳聰目明」。聽覺敏銳眼力佳,習慣上常與睿智畫等號。反之,「昏」意為看不清楚,「聵」原指天生耳聾,「昏聵」就從眼花耳聾引申為「腦子瓦特了」。
人類是視覺優先的物種,多數信息的獲取和交流來自視覺,也因此,許多常用語如「短視」、「高瞻遠矚」、「昏聵」都源於無殘障人類的角度。其實看不清晰、聽不分明,並不像胡適筆下的差不多先生,腦中一團泥漿。我曾有個學生,先天失明,每次上課一絲不苟,噼噼啪啪用小小的盲文機器做筆記,時常打斷我,請我詳細描述PPT上的圖片,期末取得優異成績。在更廣闊的世界裏,許多動物並無耳、眼一類感知聲音、光線的器官。比如吸血的蜱蟲對溫血動物的體熱、體味非常敏感,視覺和聽覺卻很糟糕,可謂「昏聵」,卻仍然成功存活繁衍近一億年。
普立茲獎得主Ed Yong的新著《An Immense World》綜合動物學研究成果,討論umwelt(直譯「環境界」)。它是某一動物所能感知的世界──牠的主觀世界。大千世界雖充滿色彩、聲音、氣味、電場、磁場等等,一個物種因其感官功能的局限,只能感知其中一小部分。比如蜱蟲的主觀世界只有觸覺和嗅覺。如果你可憐牠活在昏暗和靜默中,不妨想想自己:人類的主觀世界裏沒有紅外線、紫外線、超聲波、電磁場。連紅外、超聲這類詞語都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對眾多感知系統異於人類的鳥類、鯨類、昆蟲、蝙蝠而言,這些「超」和「外」僅僅是正常的聲與光而已。
但Ed Yong並非要證明物種彼此間的優劣。以聽覺為例,多數昆蟲如蜻蜓、蜉蝣沒有聽覺器官。拜長年進化之賜,那些有聽覺的昆蟲(如一些蝴蝶),聽力大多微調至天敵(如當地食蟲鳥類)的音高和音頻範圍內。換言之,動物的感官功能與其生存繁衍之需有關。一隻蜱蟲想把小日子過好,無需耳聰目明。即使在黑暗中,牠也能遠遠聞到溫血動物的氣息,管牠是騾子是馬還是米老鼠,管牠高低肥瘦紅橙黃綠,都意味着佳餚。
當然,你可以反駁說,蜱蟲這種低等動物要求不高,當然不用複雜感覺系統。然而,自封為「高等動物」的人類,會不會被能夠感知磁場的鳥類、昆蟲視為笨笨?為何人類不能像《封神演義》裏的千里眼、順風耳,像漫威漫畫和電影宇宙中的超級英雄夜魔俠?夜魔俠的耳朵有超準確的定位能力,還能聽到附近人的心跳。不過,動物學家指出,動物的感官功能是根據生存需要進化而來,使該動物可從環境中獲得足夠有用信息。沒有任何一種生物可以感知一切,也無此必要。試想,若人人皆成夜魔俠,聽得到彼此的心跳,那麼每天耳中所聞,前後左右,一片砰砰嘭嘭咚咚,夾雜着心梗的呻吟,房顫的雜音,把日常有用信息盡數淹沒,是不是一點吵鬧,十分尷尬?人類的存活不必如此靈敏的耳朵,就像蜱蟲無需明亮的眼睛一樣。物種各有所需,所以感官各有強弱,各適其所,由此構成千姿百態、多種多樣而非我優你劣、此高彼低的世界。
可見,在廣大的動物界,耳聾目盲並不意味着蠢笨低能,只有以視覺為主要感知器官的人類,才將視力、聽力與智力掛鈎。何況外界刺激不等於有效信息。「屈平疾王聽之不聰」,就是楚王有耳無腦,甘受蒙蔽。中國史書有個套路:大人物倒台或小人物倒霉前,總會有人去勸他及時收手或改過,而他總是不聽。《史記·商君列傳》寫商鞅在秦國為相十年,樹敵眾多。一個叫趙良的人勸他,「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但「商君弗從」,不久被滅族。
聽力過於敏銳,有時並非福氣。譬如我耳朵尖,風聲雨聲,聲聲入耳,所以為屏蔽室外噪音和家中人、貓打擾,讀書、睡覺常要佩戴耳塞。傳統戲曲劇目《打金枝》,故事出自《資治通鑒》安史之亂後四年。唐代宗化解女兒、女婿矛盾,對戰戰兢兢的親家郭子儀說:「鄙諺有之:『不痴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這句俗諺古已有之,戰國時著作《慎子》逸文:「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隋書》寫有人告發某官員誹謗朝廷,隋文帝大怒,大臣長孫平勸他寬宏大量,也說「鄙諺曰『不痴不聾,未堪作大家翁』。」可見適時耳聾是齊家治國的妙方。
「環境界」像個感知氣泡,我們都不知不覺為這個氣泡限制了感知力、思維和行動,以為自己所見所聞所感的就是世界的一切,以為其他人、其他動物也能感到同等類型和強度的外界刺激。跳出這個氣泡很難,氣泡之間的交流也不易。譬如,通常只有自己大病一場,經歷了常人未曾經歷的之後,才能對他人的病或殘障感同身受,表達出真正的同情和行動。通過想像、思考和經歷,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擴展自己的主觀世界,使它變廣變深,充滿謙卑和同理心(empathy)。能感受的多了,能想的、能做的也就相應更多。
想一想:如果要與一隻沒有聽覺、壽不過數日的蜉蝣交流,或者自己化作一隻蜉蝣,會是何種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