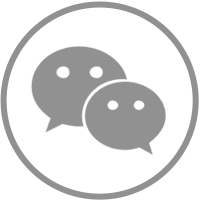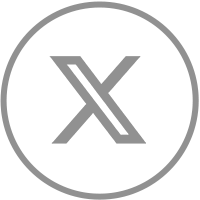偶然說起,突然意識到:講到駐港生活的開始,已經是整整十年前的事了。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拖着行李箱由廣州坐火車抵達香港九龍。那是一個燠熱的下午,陽光溫熱黏稠。此前多次來港出差,但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香港市民去「柴米油鹽」、去早九晚五,感受還是大不一樣。
周六花了一整天收拾行李,很快就把公寓佔滿了。房間不到四十平米,兩室一廳,五臟俱全,桌子是可摺疊的,還有一件我從未見過的「胖傢伙」,同事告訴是抽濕機。後來我才知道,三四十平米的房子、可摺疊傢具(甚至還有夾在窗框的晾衣杆)、三面靠牆的床、抽濕機都是多數香港家庭的「標配」。所謂「千呎豪宅」則一百來平米而已。
想看電視,遙控器從頭按到底,全是粵語節目,偶有一兩個英文頻道。粵語節目雖有字幕,但灌進耳中聲聲不識。呆坐沙發上,那一刻,我是多麼懷念央視的《新聞聯播》啊!畢竟那裏有熟悉的聲音、熟悉的語境和表達方式,想想就親切。下樓到小超市買水果,三顆進口布冧竟然花了九十多港元,又是一個沒想到!
九月一日,第一天上工。辦身份證、手機卡、八達通、銀行賬戶,一環扣一環──有了身份證才能辦各種實名卡證,而銀行賬戶還需帶有住址的繳納水電燃氣等賬單作輔助證明──陸陸續續花了一個多月才辦妥。忙亂、茫然,居港生活就這樣開始了。一個月後,眾所周知的「躁動」開始,持續七十九天,其後幾年又發生烈度更重的「狂躁」,一一親眼目睹,心裏總是緊繃着憂慮着,不敢有絲毫放鬆。直至二○二○年「七一」終於迎來安定的日子,面朝大海我淚流滿面。
儘管見過香港一度的「黑暴」,為此痛心扼腕,但對這座城市情懷未變。在港共事的「戰友」話當年,無一不對她一往情深,滿滿的都是對她的疼愛。很多人現在從事的工作已與香港無關,但一直惦記她掛念她,眼睛從來沒離開過她。香港情結,一旦結下,就是一輩子。
初來港,孤獨感漫天遍野,足足用了半年時間去克服。偌大一座七百多萬人的城市,常常感覺只有自己一個人──一個人默默走過熱鬧的德輔道、皇后大道,坐在海邊椰樹下看海,直到把夕陽看到落山,把燈光看到闌珊,把晚風從燠熱看到清涼;夜晚一個人坐在街角長椅上,街邊酒吧傳來老外的說笑聲──彷彿與我兩重世界;加班到半夜一個人登上叮叮車(子夜時分幾乎獨享「專車」),沿着古老的鐵軌,咣噹咣噹緩緩駛過西環海味街、上環西港城轉角、中環寫字樓群、灣仔軒尼詩道的市井、銅鑼灣商業區、黃泥涌道跑馬場……霓虹彩光透過木梗窗一幀幀閃過,香港的煙火味、香港的時尚範兒、香港的古舊氣、香港的喧鬧與靜謐……一一掠過,回到宿舍,唯一有聲音的是電視機,唯一會呼吸的是一枝綠蘿。
半年間,除了與同事朋友在一起,周六日差不多當兩天啞巴,沒有任何交流。一度左耳聽力莫名減弱一半分貝,聽別人的聲音感覺特別遠,反應也好像遲鈍了。回到北京到處看醫生,說可能是精神因素。突然一天感覺聲音清晰了,就這樣好了。
港漂生活以一種帶着壓強的加速度讓我們學會了與自己相處、與自己對話、開導自己。及至後來,對於獨處甚感享受。這何嘗不是一種成長呢?強韌的生命從無孤獨這一說。
好在香港擁有溫熱的情誼,來自同事朋友故交新識,也常常邂逅普通市民的善意。與Great Wall先生在元創方喝咖啡,與Sun先生在美術館賞字畫,與Chloe邊行山邊說悄悄話,與Wong先生在饒館觀荷品茗、與Connie在九龍吃意麵看海天雲色、與劉太去元朗參觀文天祥後裔大夫第、與石先生在旺角茶樓吃點心聊天,在Ng大哥的office聽他在港打拚的傳奇故事,在上環老舖與M兄等圍爐夜話,在黃Sir的農莊BBQ,與朋友到大嶼山西貢行山看海,與小樂聊葛亮的書……香港動盪時,同事陪我步行,戴大哥站在樓門口目送我進門;疫情嚴峻時,WG、敏姐等四處淘來口罩勻給我……
許多個周六日,一人全套流程包上百隻餃子凍好送朋友,廣受歡迎,於是買好食材聚朋友家一起包,其樂融融;曾在端午節當義工,到劏房給基層市民送糉子,爬了五座樓幾百階樓梯,還有九層樓頂上的鐵皮房;曾探訪公屋老婆婆,去塔門島看漁村龍舟賽與漁民用粵語傾偈;曾與一群年輕人從下午談到晚上足足六小時,聆聽他們的苦悶;曾與九○後女孩一人一個飯盒從晚上七點半聊到十一點多,幫她開解心結……
一眼十年,一念永遠。當年隻身赴港,留下了點點滴滴,無怨無悔。「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香港這片土地,對於我們,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