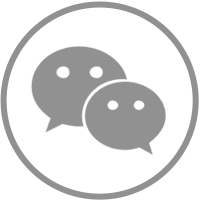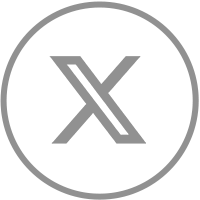國慶這個節日,除了其共性意義,於我還有兩個特殊之處:一是,有個七天長假,與春節長假不同,它不會被走親訪友、迎來送往充斥,是出遊的好機會;二是,十月二日是兒子生日,「大生日」、「小生日」一前一後,從他懂事起,我就不止一次提醒兒子他的生日與這個節日的親近關係。多年來,我家都是兩個「生日」一起過。在他少年時,過生日的方式便是旅行。
印象最深的幾次,是帶他遊歷了「四京」。所謂「四京」,是指北京、南京、開封、西安。「四京」之說,源於第一次帶他去北京看國慶升旗。
天還沒亮,看升旗的人已經漆漆一片。天安門廣場,每人都手握一面小國旗,儘管身上有大包小包,卻都會騰出一隻手來。我把兒子托上頭頂,我看不到國旗如何升起,但我能感受到,因為兒子不停地晃動手裏的小旗,小嘴不停地向我「轉播」。隨着他一聲驚喜地呼叫,我知道升旗儀式開始了:「爸爸,你看到了嗎?五星紅旗升起來了。」我說看到了,其實我只能看見他手裏的小國旗,隨着它搖動頻率的增強,我知道鮮艷的五星紅旗在越升越高。那一刻,內心的激動無法言表──當我把兒子托舉起來的時候,我知道我們之間已完成了一個信仰的接續。
就是那次,他問我,爸爸,中國有北京、南京,為什麼沒有東京呢?我說有啊,東京在河南,那個城市叫開封,宋朝時叫東京,也叫汴梁、汴京。是這樣啊,他又問,可是,怎麼沒有西京呢?我說也有,西安就是西京,在賈平凹的小說裏,西京就是西安。歷史上,它們都是我們這個國家的都城。兒子說,我想把這四個京城都去一遍。於是,我們的國慶旅行就有了特殊的主題,也是從那時開始,他的生日基本都是在外地度過。
去南京是他第一次遠行、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在外地過生日,總之,收穫了很多第一次;在西安,他體驗了一輩子都難忘的顛簸之苦──別說卧鋪,就連硬座票都沒買到,幾十個小時的火車全程站立,有一段他還算幸運,我把他放在了車廂的盥洗盆裏;去開封那次,終於買到了卧鋪,我們一路睡得很香,差點坐過了站,而回程彷彿是對去程的呼應,又險些誤了火車,當列車員把氣喘吁吁的父子倆拽上火車時,火車已經緩緩啟動。國慶的「四京」之旅,奠定了他以後的路,他成了一個見多識廣的孩子──他對這個國家很熟悉了。
這樣的國慶出行,直到他考上大學,被他的返鄉所取代。大一那年國慶,是我最為期盼的一次,用望穿秋水形容也不為過。那是他第一次離開我們在外學習和生活,這和有我陪伴的短暫旅行不一樣。和許多送孩子去上大學的家長一樣,離開校園時我哭了,儘管我把頭仰得高高的,假裝看天上的白雲,眼淚還是順着臉頰流下來。後來他也說,當時他回了好幾次頭,都只看到我的背影,那時他也哭了。那年,盼他國慶放假回家,成了我整個九月最大的心事。
以此為起點,再到他參加工作、在外地生活,國慶這個節日,便成了鐵打的返鄉之日。從過去的帶兒出行,到現在的待兒返鄉,完成了我家國慶節主題的更迭。其實,不光我家這樣吧,國慶這個節日,出遊與返鄉,應是絕大多數家庭的共有主題。在這樣的日子裏,有多少人會離開自己的小巢,飛向更廣闊的天地,又有多少遊子,如鳳還巢,回歸家庭的懷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