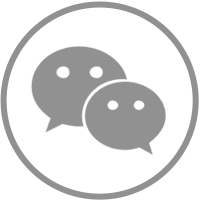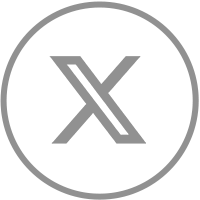一九○四年,二十一歲的劉師培給《警鐘日報》寫文章《論白話報與中國前途之關係》:「自吾觀之,白話報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話報推行既廣,則中國文明之進步固可推矣;中國文明愈進步,則白話報前途之發達,又可推矣。」──此時距離第一份白話文報紙《無錫白話報》創刊,裘廷梁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只有六年,這六年裏白話文的推廣和普及一直在悄悄地進行着,《杭州白話報》大受歡迎,江西有《新白話報》,上海有《中國白話報》(林白水主編,劉師培為主要撰稿人),陳獨秀剛剛創辦了《安徽俗話報》。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天津的《大公報》、香港的《中國日報》這些傳統大報,也開始使用白話。
白話到底有什麼好處呢?劉師培總結為兩條:一是救文字之窮,「吾觀鄉里愚民,無不嗜閱小說,而白話報體,適與小說相符,則其受國民之歡迎,又可知矣。」二是救演說之窮,「演說之設,僅可收效於一鄉,難以推行於極遠,是演說之用,有時而窮。若白話報之設,雖與演說差殊,然收效則一。」因為淺顯易懂,所以受眾廣;因為接近口語,所以傳播快。這的確是白話報紙受歡迎的重要原因。
作為新興之書面語,白話當時面臨兩重疑惑,劉師培也有清晰的分析論斷。第一,方言不應的問題,他說,「欲統一全國語言,不能不對各省方言歧出之人,而悉進以官話。欲悉進以官話,不可無教科書,今即以白話報為教科書,而以省會之人為教師,求材甚易,責效不難,因以統一一省之語言,而後又進而去其各省會微異之音,一馴致全國語言之統一,豈非大得其益而不足為病者與。」這不就是十年之後胡適所言「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嗎?第二,用字太繁的問題。「此非白話之咎,而論者錮於文言之過也。今印術發明,日出萬紙,復何所吝,而必則古昔。且持文言之書而講解之,必補入無數語言,始易了解,事同翻譯,故非盡人可能演為白話,則識字者皆能之矣。」他最後的結論是,「取二善,去二疑,則白話報之有益於文化可知矣」。
劉師培生於江蘇儀徵的經學世家,其曾祖劉文淇、祖父劉毓崧、伯父劉壽曾、父劉貴曾都是著名的學者,劉氏家學兼具吳(惠棟)、皖(戴震)兩派之長。他聰穎異常,十二歲遍覽四書五經,詩文稟賦很高,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未冠即沉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任」。
雖然大力提倡白話,但他卻從未排斥反對文言,一九○五年與鄧實、黃節等發起組織上海國學保存會,出版《國粹學報》,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舊學之長,年輕人接受外來新思想的敏銳,短時間內撰寫了大量著作,除《中國歷史教科書》外,還有《中國倫理教科書》《經學教科書》《地理教科書》《文學教科書》等。劉師培為今人熟悉者,是他在北大做教授時的講義《中國中古文學史》,受到魯迅的推崇。
劉師培命途多舛,早年思想激進,提倡無政府主義,後加入籌安會贊同袁世凱稱帝,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北京去世時年僅三十六歲。陳獨秀安葬了他。身後留下諸多著述,經錢玄同、劉文典等整理,一九三六年出版了六函七十四冊《劉申叔先生遺書》。他講學時間雖然不長,成都國學院一年,北大兩年,卻也培養了不少學生,劉文典、蒙文通、陳鍾凡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