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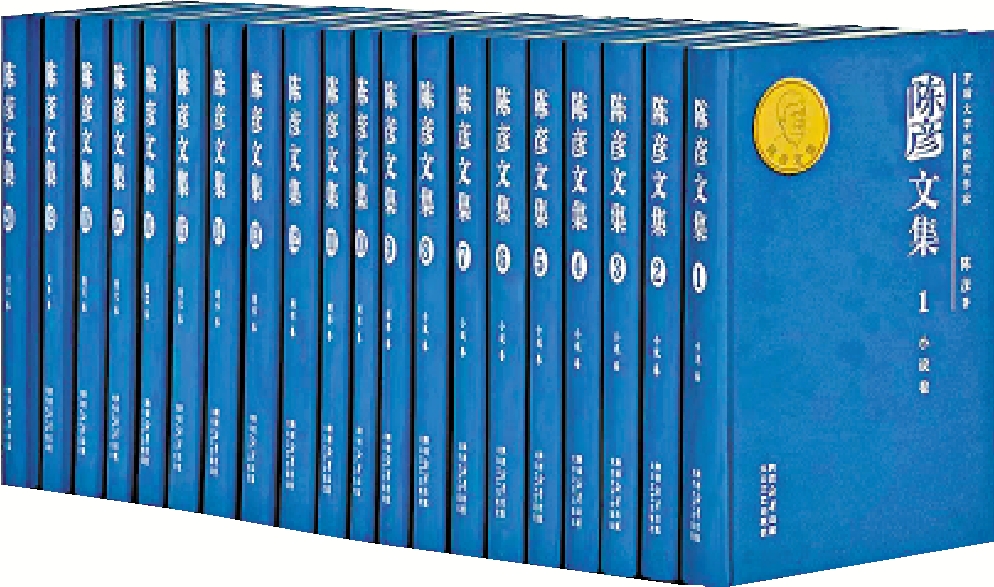
在中國當代文學界,作家陳彥被認為是「近年最大的發現」,其每部作品都保持了很高的藝術水準。用評論家吳義勤的話說,陳彥扎實的寫實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蘊、細膩的人物塑造、綿密的敘事風格賦予其小說獨一無二的品格,「給了中國文學一個又一個驚喜」。
去年,這些「驚喜」匯集成《陳彥文集》二十冊,由內地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陳彥的首部文集。從十五六歲時受青年人都愛文學的風潮「誘惑」,湊熱鬧一頭扎進去,到如今作品等身,陳彥近日接受《大公報》專訪時總結稱:「生活根基是一個作家寫作的基礎,作家得培養這個『營養菌群』。如果沒有生活這個『酵麵』,肯定是蒸不出「白麵饅頭」的。」\大公報記者 張帥
與專職小說創作的作家不同,陳彥具有「戲劇家」與「小說家」的雙重身份,其首部長篇小說《西京故事》先寫的舞台劇,感覺言猶未盡,遂又寫成了一部同名長篇。在陳彥看來,小說與戲劇是互補的,好舞台劇思考的深度和寫作的技巧,值得小說借鑒。
戲劇與小說「兩棲」
他的小說常常把戲文信手拈來,有時自成一體,為人物量身打造一段唱詞嵌入文本。越劇《人面桃花》的戲文「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在小說《裝台》中反覆出現。《主角》裏秦娥在古城牆奔走呼號,用一連串的胡板苦音升起一段段肝腸寸斷的秦腔:「夜沉沉,風嘯嘯,漫天楊花作雪飄……唯留春風當剪刀」。最新長篇小說《星空與半棵樹》更是以戲劇開頭,又以戲劇結尾,並在重要的關目安排了一幕活報劇。
「戲劇是戴着鐐銬跳舞的藝術,時間空間不允許你拉長伸展,大拆大卸。長篇小說更像是開出一條河流,有九曲十八彎,有靜水深潭,有飛流直下,有百轉千回。小說與戲劇應該互為依存、相得益彰,它們都需要講好故事,塑造好人物形象,也都需要在故事和人物背後折射精神思想與哲理的光芒。」陳彥說。
做生活的「有心人」
陳彥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擔任過二十五年專業編劇,交叉任職過十幾年團長、院長。創作《裝台》時,為了寫好農民工群體,他經常穿梭在西安的勞務市場,認識了大量為劇場翻台的「裝台人」,他們身上裹挾的血肉經驗成為小說鮮活的素材。也因為與戲劇舞台上的各類「角兒」打了半輩子交道,對他們的生活如此之熟悉,讓陳彥在寫《主角》時經常「一瀉千里」,《喜劇》的創作也同樣如此,這三部小說組成了他的「舞台三部曲」。
寫作方法有千條萬條,最根本是對生活熟悉,對不熟悉的生活,一個字也編不出來。陳彥說並非必須親身經歷,而是要用各種辦法去努力接近書寫對象,「最終骨骼與皮膚都可感時,才能下筆。」經過長期「滷水發泡式」的生活體驗,只要閉起眼睛,許多人物就會開始走動、說話。評論家李敬澤曾評價,讀陳彥的作品,裏面的聲音與語調都不是外來的,「它就是這個世界內部的聲音」。
「每個作家都要依賴生活的『庫存』,無論他怎麼表述,沒有生活這個『酵麵』,肯定是蒸不出『白麵饅頭』的。」在陳彥看來,生活根基就是一個作家寫作的基礎,作家得培養這個「營養菌群」,如果能再做個「有心人」,那麼就能將「庫存」的邊界擴得更大。在此過程中,重要的是自然地去體味,置身其中,而若刻意,反會着痕跡,只能得到生活的表皮。
為「小人物」立傳
閱讀「舞台三部曲」,裏面看似聚焦演藝人生,其實都在講述人間百態。如陳彥在《主角》的後記中所說,戲劇讓觀眾看到的永遠是前台,而他努力想讓讀者看幕後,就像當初寫《裝台》,觀眾看到的永遠是舞台上的輝煌敞亮,而從來不關心、也不知道裝台人的卑微與苦焦。他始終認為,「大人物」的生命世界裏已經塞滿了太多的好東西,因此應該把希望、美好與力量,賦予更多「小人物」。
寫「小人物」的故事,並非是要人勵志。陳彥指出,「人民創造歷史」不是一句空洞矯情的話,它是人類過往歷史的基本形態,司馬遷《史記》裏最精彩的部分,常常是那些普通身影的驚鴻一瞥。而世間一切偉大的藝術,必然與天地,與眾生緊密相連。換句話說,只有關注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命狀態,才可能成就一門偉大的藝術。
「無論文學還是戲劇,都不能缺失悲憫與人道情懷,更不能缺失對混沌,甚至幽暗生活的點亮。」陳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