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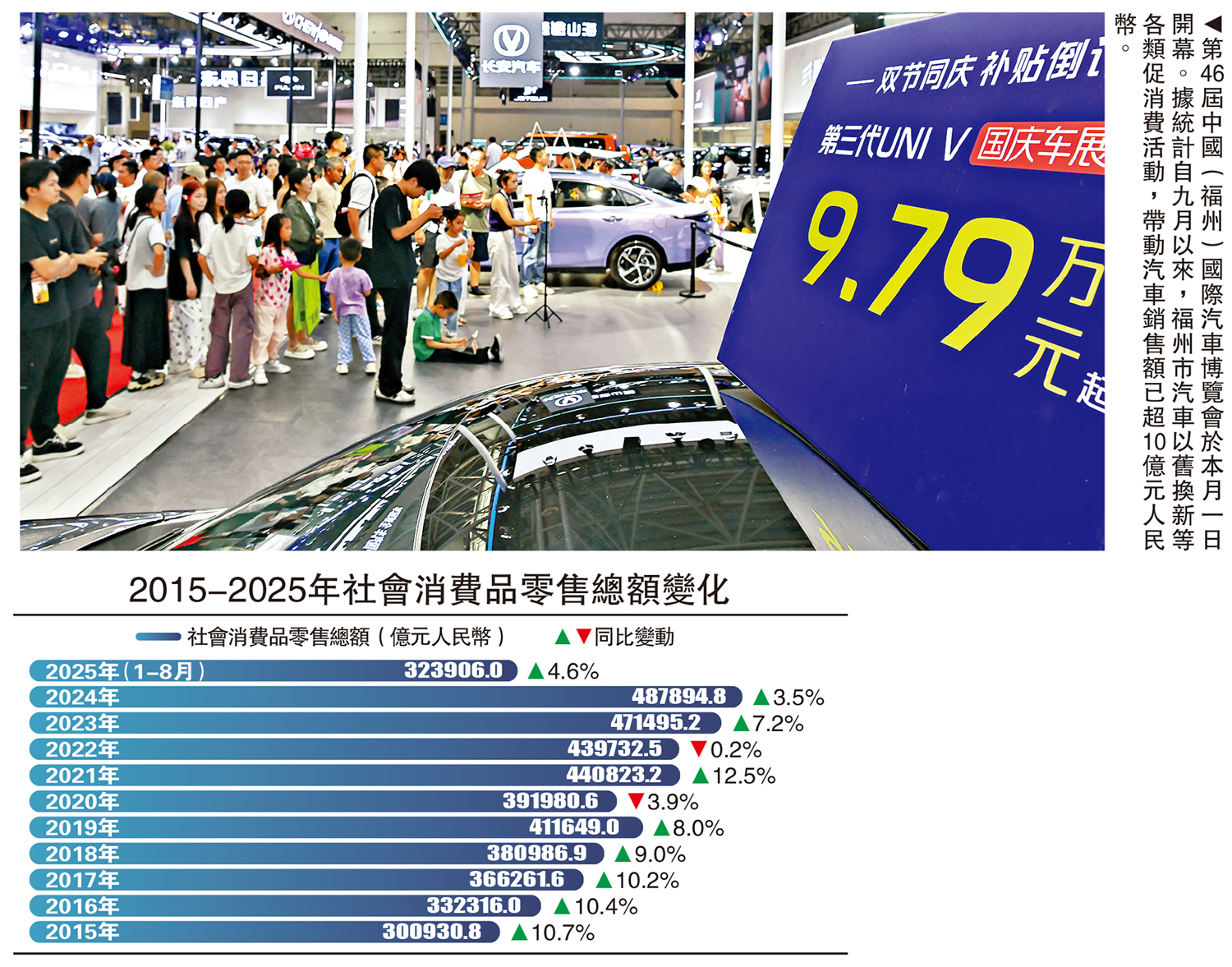
近期關於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優先支持消費還是投資,仍然存在不少爭論。在筆者看來,短期刺激總需求與長期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並不矛盾,當務之急是選擇乘數效應更大的政策工具提振需求。
不少有影響力的學者指出,各類經濟增長模型均表明長期增長的關鍵在於通過擴大再生產提升總產出,這一過程或者依賴要素投入,或者依賴效率提升,因而不存在「消費驅動」的長期經濟增長模式。投資,特別是基建投資應該是當下政策優先支持的領域。
筆者認為,面對中國經濟當下就業不足、價格下行壓力較大的挑戰,當務之急應該是刺激短期的總需求,而非只看重總供給的長期影響,刺激消費在這方面優勢明顯。
即使關注中長期經濟增長,中國投資相對消費的比例也已經顯著高於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水平,而且造成產能過剩的情況。綜合考慮屬於消費的人力資本投入回報高於物質資本,且政府主導的許多投資還可能無法形成經濟學意義上的「有效供給」,筆者以為若當下財政支出如果能有增加,仍然應該首先加強對消費的支持。
刺激消費乘數效應較高
首先從理論上講,雖然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取決於總供給擴張,但是由於短期存在多種類型的衝擊,由總需求決定的實際產出只是圍繞由總供給決定的潛在產出波動,兩者並不嚴格一致。在一些情況下,讓總需求向總供給自然靠攏可能曠日持久,會出現較長期的就業不足或通貨膨脹。宏觀調控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對此進行干預,平抑經濟周期。
從這個意義來看,當前中國宏觀政策的主要目標應該是較快提振中國的總需求,緩解價格下行和就業壓力——中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已經連續三十多個月低於1%,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更是連續近四十個月負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何種類型的財政支出有更大的乘數效應和槓桿效應就應該被優先考慮,而是否能增加長期的總供給只能處於次要地位。
筆者以為,若財政政策在改善社會保障、提振服務消費等方面發力,效果應該明顯好於用同等規模的資金支持投資或是基建投資。比如,如果能夠更好的改善中國居民的養老、醫療、失業等領域的保障水平,不僅僅財政在這些領域的直接支出會提振消費增長和總需求,中國居民的預防性儲蓄也會下降,會通過槓桿效應進一步推動總需求走強。
實際上,2023年中國居民總儲蓄率高達34.9%,在主要經濟體中居於首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而政府增加基建投資則不具備這種槓桿效應。同時,如果財政支出對服務業消費等實施刺激,由於服務業的供給要素主要是勞動力,服務業消費支出走強會直接帶動一般民眾勞動報酬的上升,並且進一步拉動消費,政策的乘數效應較高。
反過來,基建投資增加之後,勞動收入的份額僅佔一小部分,大量收入成為了資本的報酬,還存在各類跑冒滴漏。由於富裕人群的消費傾向較低,而國有企業利潤對公共財政的繳納比例也不高,基建投資的對總需求的乘數效應偏低。因此,從應對中國經濟當前最大的挑戰——總需求不足——的角度來看,筆者以為刺激消費更有效率。
其次,即使考慮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在投資和消費之間的取捨也需要考慮社會福利的影響。理論上講,經濟發展和增加產出的根本目的在於提升以消費為代表的福利水平,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因此,雖然擴大產出的關鍵在於增加投資,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一個經濟體就應該把幾乎所有的資源都用於投資。否則,就會犯下「為生產而生產」、「把手段當作目的」錯誤。即使是從犧牲當前消費,換取未來更多的產出和消費的角度出發,消費和投資之間也應該有個合理的平衡。
實際上,宏觀經濟模型對於如何實現兩者平衡已經有很明晰的指引。由於利率是調節一個社會消費和儲蓄(投資)的槓桿,學術界普遍認為,實現長期福利最大化情況下投資和消費的分配應該遵循利率的「黃金法則」——即社會的中性利率水平應該大體上與這個國家的經濟潛在增速相匹配。如果社會的中性利率低於潛在增速,意味着當前消費不足,投資項目過多且回報偏低,進行這些投資並不划算,降低了社會福利;反過來,利率如果高於潛在增速則意味着當期消費過度,投資不足,未能充分捕捉經濟體系中有回報的項目來擴大再生產,影響未來產出擴張和消費增長。
數據顯示,從長期來看,發達經濟體的利率水平基本上符合黃金法則。例如,根據世界銀行披露的數據,美國在2000年至2019年期間,實際利率中樞為2.85%,實際經濟增速中樞為2.11%,兩者偏差0.74個點。英國在1995年至2014年期間,實際利率中樞為1.43%,實際經濟增速中樞為2.22%,兩者偏差0.79個點。然而,中國的中性利率較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明顯偏低。比如,從2009年到2019年,中國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比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增速低約4.8%。
過度投資恐釀產能過剩
這意味着,由於社會保障不健全等多方面的因素,中國的消費水平已經明顯低於理論上福利最大化的消費水平。筆者以為,這也是中國居民對經濟增長獲得感不強的重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擴大投資,全社會的福利損失只會進一步擴大。實際上,由於國有企業和政府投資的資本回報低於社會平均回報,為了政府項目的投資而犧牲當前消費造成的福利損失可能還要更高。反過來,如能用增量財政資金對消費進行支持,反而有利於中國經濟糾正扭曲,改善全社會的福利水平——這也是回歸發展經濟的「初心」。
過度投資也會造成產能過剩。當前中國經濟存在規模較大的產能閒置。上半年,中國製造業產能利用率為74%,是2017年以來同期新低(除2020年外)。今年1月至8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銷率也是2001年有統計以來同期最低。產能過剩加劇企業低價競爭、利潤和現金流萎縮,進而可能引發就業萎縮、殭屍企業等一系列風險,這也反映出依賴供給端的經濟發展模式仍待進一步轉變。
加強人力資本投入
再次,筆者以為即使希望通過投資提升總供給,推動中國經濟中長期更好的增長,也應該選擇投資回報更高的領域。數據顯示,當前投資中國人力資本的回報高於物質資本。政府新增財政支出與其投資於物,不如投資於人——這也符合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於人』」的表述。眾所周知,產出的擴張不僅僅取決於公路鐵路橋樑等基礎設施和設備廠房等物的因素,也取決於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工作經驗、體質健康等人的因素。
根據清華大學有關課題組的研究,1978年至2020年,中國提升各教育階段毛入學率所需新增的教育投資帶來的宏觀教育回報率,高於經濟學文獻測算的同時期平均物質資本投資回報率。即使是考慮當下,測算得到的高中、大學和研究生階段教育投資的宏觀回報率分別為27.1%、20.9%和21.6%,也遠高於201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測算的中國經濟5%的物質資本投資回報率。
然而,在目前的統計制度中,包括教育、醫療、育兒等人力資本領域的支出都被歸於消費。從這個意義上說,支持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消費,遠比支持基建投資更有利於中國總供給的擴張和長期的經濟增長。
總體而言,無論是從中國經濟短期彌補供需缺口、提振價格和就業來看,還是從改善社會福利和更有效的提升中國中長期供給能力來看,增加政府資助乃至主導的基建投資都不見得是優於促進消費的政策選擇。反過來,利用增量財政資金刺激消費,補強醫療、教育、生育、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短板,提升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投資於人、改善中國民眾對經濟增長的獲得感,才是當務之急。
(作者為京東科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